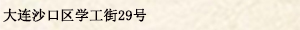河北人简史
山东人、四川人、山西人、天津人
广东人、浙江人、湖南人、北京人
都能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
河北人
不仅外人认知不清而且自我认同模糊
“河北人”到底是什么?
“河北人”经历了什么?
从慷慨悲歌,到沉默隐忍
撰文|高昌绘图|孟凡萌
“河北人”现实中识别度有多低?
“河北人”,跟“河南人”、“山东人”的有着相同的定义套路:说的就是以行*区划的河北省为地域形成的群体,一般包括生长与此,并与河北有故乡关系的人,也包括部分长期在此工作生活并对这里产生认同的部分外来人。
我在北京工作,是个地道的河北人。
不过,跟其他兄弟省份相比,我们河北人有这样一个尴尬境遇:全国各地有各种各样的同乡会组织,却几乎没有“河北同乡会”;现实中,我们甚至说不清“河北话”、“河北菜”的概念。诚如河北省文联副主席郑一民先生所说:“说起山东人、河南人、山西人,都会有一个大致的性格判断(虽然未必准确),但对于河北人,外人却很难有清晰的印象。我们往往是在离开河北后,才意识到自己的‘河北人’身份。”
网络世界对河北人似乎也讨论不清,说的最多的往往是:河北人形象模糊糊,说不清有啥特点。
河北人与行*区域的河北密切相关。河北,顾名思义,来自“*河以北”。不少人,包括许多河北同乡觉得,“河北”一词是近代才诞生的,其实它来自唐代设置的“河北道”,管辖范围与今京津冀地区大致相当,囊括了今山东省、河南省*河以北的地区,甚至一度管辖东北。宋代沿用了唐代名称,称为“河北路”。到了元、明、清三代,河北区域变成了中书行省、北直隶省、直隶省——因为了有了直属中央的待遇,“河北”这个词,逐渐被淡化了。
至年国民*府南迁,“直隶”才还名“河北”——此时距离唐代“河北道”设置已年,距离宋代设置“河北路”将近年。不过,这个最早的“河北省”,仅存在了几天便被拆分,北部分别划归热河、察哈尔两省;至年,冀南5县划归平原省;年、年,察哈尔、热河省撤销,原属地重归河北,今天的河北省于此时方见雏形(姑且不论后来划归京津之地)。
由此可见,河北的历史积淀深厚,但长期处于分分合合中。唐代“河北”与近代之“河北”已经相隔千年之久。可以说:“河北”这个词虽然悠久,但没有形成持续的积淀的历史。在人口稠密的东部各省中,河北的地理单元最多元。我曾在一则赋中描述它:“燕赵焕彩,宝地福天。南望*河,北控燕山。太行西倚,沧海东观。”冀北有燕山山区、坝上高原,冀西有太行山区,冀中南为河北平原,冀东北则是滦河平原,海河、滦河出山麓不远就是海滨……
这就是河北:破碎的历史、复杂的地理,交织在一起的行*区域。这样一来,河北人的形象传播,很难形成传播学上说的“轰炸性”“冲击力”。
四川、河南、山西、浙江这些省份,相对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的行*版图相对稳定、历史名城也少有变化,山西虽然很长时间叫“河东”但核心区域一直都是一体;浙江也曾经叫“两浙路”,但现有地域从未被隔离。
“河北人”的尴尬,很大程度是这么造成的。
“慷慨悲歌”:是河北人的 道烙印
那么,河北人真的没特点可说了吗?非也。河北人不仅有特点,而且个性鲜明,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在外地也有口皆碑。
生于江南、成名于香港的金庸先生笔下的“侠之大者”乔峰,被描述成“燕赵北国的悲歌慷慨之士”。金先生在书里借段誉之口说:“好一条大汉!这定是燕赵北国的悲歌慷慨之士。不论江南或是大理,都不会有这等人物。包不同自吹自擂什么英气勃勃,似这条大汉,才称得上英气勃勃四字!”
乔峰这个“燕赵人”虽是虚构,但“英气勃勃”一词道出了古代河北人的最鲜明特征。古代文献中,河北人的特征不仅不模糊,反而是形象最为鲜活的群体。今人常说“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说的就是河北人。这话最早出自唐代文学家韩愈的《送董邵南序》。“慷慨悲歌”,也是河北人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 道烙印。
韩愈的这句“总结”绝非心血来潮,而是有历史依据的:他撰文之前,唐贞观年间完成修纂完成的《隋书·地理志》中说,燕赵一带“俗重气侠”、“自古言勇敢者,皆出幽并”。幽并,即古幽州、并州,地域大致包括今河北中北部到山西太原一带。汉末诗人曹植就有诗云:“君是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慷慨”、“侠气”的河北人,还具备“忠义”的品格。曾经,几乎中国每个古城内,都有一座“三义庙”。“三义”就是刘备、关羽、张飞。当年,三人结拜之地就在河北涿州。刘、关、张三义,河北人占了三分之二(刘、张卫河北人,关羽为山西人)。燕赵大地上,像这样的忠义之士还有正定常山人赵子龙、闻鸡起舞的河间人祖逖、中流击水的无极人刘琨等英雄人物。
写下“忠义”传奇的不仅有武将,也有铁骨铮铮的文臣,河北容城人、明朝谏臣杨继盛是其中的佼佼者。杨继盛先后上疏弹劾奸臣仇鸾、严嵩,他当众大骂权倾朝野的严嵩是“天下之 大贼”,即便在狱中被打得血肉模糊仍“意气自如”(据《明史》)。台湾作家李敖在《北京法源寺》中写道:“清代读书人,几乎无人不崇敬杨继盛,也无人没有读过他的这两篇正气凛然的奏疏。”
我还在网上看到一句别人写的顺口溜:“东北虎,西北狼;河北人,小绵羊。”这话极力形容河北人太老实,甚至性格绵软。老实——的确是河北人的一面,但要把其比作“小绵羊”,说起绵软,未免就有些无知了。
君不见,战国有七雄,河北的燕、赵居其二,燕昭王、赵武灵王均是一代英明君主;君不见,汉末三分天下,蜀汉昭烈帝刘备和其手下猛将张飞、赵云,都是河北人;君不见,东晋名将祖逖、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那也都是响当当的河北汉子!
古人虽然已经远去千百年之久,但是那些万丈豪情的基因仍在河北人身上得到了发扬。清末,杨露禅、董海川、大刀王五、霍元甲等河北人,皆是一代武林宗师。抗战时期,承德一带有高唱“大刀进行曲”的长城抗战,保定有可歌可泣的“狼牙山五壮士”,国*中有孙连仲、佟麟阁这样的河北抗日猛将,广袤的河北平原上则活跃着共产*领导的平原游击队,还有马本斋麾下赫赫有名的冀中回民抗日支队。
河北诗人公木先生创作了《八路**歌》,其中词句铿锵豪迈:“一旦强虏寇边疆,慷慨悲歌上战场。”给《义勇*进行曲》作词的田汉先生,虽不是河北人,但长期生活在河北,其妻子安娥女士,是地道的河北女子。长期担任河北省文联主席的田间先生,在《给战斗者》的结尾写道:“在诗篇上,战士的坟场,比奴隶的国度要温暖,要明亮。”生于河北望都的诗人鲁煤,更是留下了这样的誓言:“为活着而斗争,或者,为斗争而死,都要一样坚决。”
试问,若了解这些,那位编顺口溜的仁兄还敢说河北人是“小绵羊”吗?我要自豪地说:河北大地虽然经历过战争和灾难的洗礼,它虽经历过“燕赵—河北道—河北路—中书行省—北直隶—直隶—河北”等不同时期的名称变更,还经历过数次行*区划的分分合合。但是,“慷慨悲歌”的传统从未失去!
“悲情”“悲剧”:河北人为何喜欢“苦情”?
“我的家乡在河北,我爱我的家乡美。太行山秀燕山俏,蓝湛湛的一湾渤海水。平川沃土稻谷香,坝上草原牛羊肥,哎嗨哎哎……”这首歌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歌唱家皮冬菊女士一度让这首《我的家乡在河北》走红。河北人内心里的那份自豪明朗、高亢大气,在深情优美的旋律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几乎跟《我的家乡在河北》同时,河北另一歌手朱明瑛把《回娘家》唱红了:“风吹着杨柳沙拉拉拉,小河的流水哗啦啦啦……”《回娘家》为了传唱需要,当时被称作“河北民歌”,它其实是从台湾歌手邓丽君那里改编的。
那个年代,邓丽君的歌在内地被称为靡靡之音,不许公开演唱,所以朱明瑛讨了个巧,以河北民歌的名义带它上了年央视春晚。不过,把《回娘家》说成“河北民歌”并非没有根据,因为邓丽君祖籍河北大名,而朱明瑛祖籍河北南皮——她们“娘家”都在河北。一首歌词俏皮的《回娘家》,把河北人风趣幽默、淳朴稚拙甚至稀里糊涂的性格,演绎得活灵活现。
邓丽君生前多次表示“想回河北看看”。可惜世事无常,邓女士终未还乡,而优美的歌声却能穿越时空樊篱,带着她的芳*回到河北的“娘家”圆了梦。不过,《回娘家》的曲调欢快流畅,但叙述的是鸡飞鸭跑的“悲剧”。
与全国其他地方的艺术作品相比,河北的戏剧、民歌似乎更乐于表现悲忍、哀伤的情绪。中国古典四大悲剧,有两部诞生在河北:《窦娥冤》、《赵氏孤儿》。河北民歌则以哭腔苦调为特色,民歌《茉莉花》在江南等地的传唱中欢快优雅,只要一用河北民歌调子来唱,就多了几分凄凉。
那首名传全国的《小白菜》也是河北民歌,其“小白菜啊,地里*啊,三两岁上,没了娘啊……”的伤感悲鸣,更是唱得人肝肠寸断、涕泪横飞。河北人 的两大剧种是河北梆子、评剧,其腔调旋律风格可说是一个阳刚、一个阴柔。
阳刚的河北梆子唱腔“悲壮”,而阴柔的评剧唱腔“悲凉”——都离不开“悲”字。评剧名角白玉霜、小白玉霜,更是擅长哭戏。这些艺术作品,正是河北人内心的折射:凄苦、苍凉、悲壮、辛酸……我也爱听家乡的戏,听着听着,就默默地有一份疑惑:为什么我们河北人总是有这么多“悲”?总是有这么多“苦”?这“悲苦”是怎么产生的呢?
很多人从“慷慨悲歌”中读出了豪气,却没有注意那个“悲”字,其实,自古以来,这里的人身上总是充满着悲情。河北历代不乏帝王将相和英雄豪杰,但多是忍辱负重之人一生多有凄惨命运。比如赵武灵王锐意改革,实行胡服骑射,但晚年居然被囚禁于沙丘,活活饿死;秦代河北人赵佗受命南下开发岭南,堪称历史上 位“南下干部”,那种苦非常人所能承受;三国蜀汉先主刘备,成就大业之前,颠沛流离,隐忍落魄,开创帝业不久就撒手人寰、白帝城托孤;西晋末年的河北人祖逖、刘琨半夜闻鸡拔剑起舞,后来从*报国,却都郁郁不得志,忧愤而死。
隔着茫茫岁月回望历史烟尘,我发现:河北人的命运仿佛是冀中平原上随处可见的野菜马齿苋,什么环境下都能舒展翠绿的叶,蔓延鲜红的茎,绽开洁白的花,耐热、耐旱、耐涝,清热解*,散血消肿,而且还可以走上餐桌包饺子、蒸包子、拌凉菜。可是,无论人们说过多少赞美的好话,写过多少优美的赞歌,它自己总是带着那么一缕淡淡的寒酸辛苦的味道,让我的心里一想起来,就平添许多凄楚和悲怆。
为什么河北人总是悲情的,我觉得 的原因是:他们性格太过刚直。古语云:“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品行高洁的人,最容易受到污损;性情刚直的人,往往容易横遭奇祸。透明、坦率、坚贞的河北人,虽然嘴上不较真,但心里少不了哀痛的情结。
河北诗人郭小川曾经写了一首长诗《一个和八个》,为被误解、被 的心灵鸣不平。后来陈凯歌根据这首诗拍成了同名电影。可是,谁能理解电影背后,郭小川和众多河北人所付出的代价和遭遇的种种不幸呢?
河北人虽命运苦楚,但不事张扬,不喜抱怨。而一系列的艺术作品,将这种苦楚、酸楚、凄楚的“悲情”呈现了出来。中国各地方戏以大团圆的喜剧、正剧居多,偏偏河北人的戏独树一帜——它们大多是悲情戏。
戏如人生。有苦不说,河北人直往肚子里吞。他们,真的堪称中国最悲情的群体。
京津强势:河北人变成“沉默的大多数”
说起河北名人,大概以金元时期为分水岭:元代以前,今河北地域豪杰辈出、人才灿如星河。随着元明清三代均以北京为都城,再伴着天津作为港口城市逐渐崛起,“河北人”的星光日益暗淡。有两方面的原因:一、 的河北人更愿意涌入这两个大城市;二、河北人的形象被邻近的光芒遮住了。
长期生活在天子脚下,潜移默化中,曾经个性鲜明、充满血性的河北人,性格中慢慢多了一些顺从、精明、平庸。北京没成为*治文化中心前,河北(燕赵)各路豪杰是全国重点治疗白癜风 的药膏北京医院治疗白癜风费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