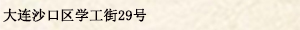王韵从后汉书知意看刘咸炘的史学观
刘咸炘(—),字鉴泉,号宥斋,四川双流人,近代蜀中 学者,受其家学熏陶,自幼聪慧好学,在他五六岁时,先后从兄刘咸荥和父亲学习。年,18岁时其父卒,改由其从兄刘咸焌(字仲韬,清光绪癸卯举人,创办成都尚友书塾)授业,年成为尚友书塾塾师。年至逝世前,先后兼任成都敬业学院哲学系主任、成都大学和四川大学教授。刘咸炘博通群籍,学贯中西,治学严谨,著述丰富,著书部,卷,总为“推十书”,其内容涉及哲学、经学、史学、校雠学、方志学、文学、宗教等诸多领域。 历史学家蒙文通极其推崇刘咸炘,在《四川方志序》中称赞他“其识骎骎度骝骅前,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
刘咸炘笃学精思,明统知类,“可惜天不假年,又远离学术中心,故其名不显,其学不彰,然而其书具在,精光自不可掩”。《后汉书知意》是刘咸炘《四史知意》的第三部成果,刘咸炘对《后汉书》中的“本纪”和“列传”进行了系统探讨,学界对《太史公书知意》《汉书知意》《三国志知意》皆有研究,而对刘咸炘《后汉书知意》还未见专门的系统论述,本文以《后汉书知意》为考察对象,从史学史角度探讨刘咸炘著史需明确史体,读史应察变观风重源流的史学观,从中可见刘氏的史学意识。
秉承章学诚的治学思想,刘咸炘的《后汉书知意》并没有着眼于文字和文法的考证,而是从史法和史识的角度探究《后汉书》的史意,并对《后汉书》的篇体和识旨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评价。杨树达在《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中对《后汉书知意》高度评价到:“平心论之,蔚宗之书难不逮马、班远甚,要不失为良史,清代治史诸家考证文义者居多,专论史法者颇少,刘氏裒录成说,特为专书,立体既新颖可人,于读范书者亦实有裨,不失为佳著也。”
一、《后汉书知意》撰写原因和体例
《后汉书知意》成于民国十九年,刘咸炘在本书开篇说到:“庚申年秋读《后汉书》,有所评议,记为一册。近修《太史公书》《汉书》二《知意》既毕,因取旧册修补为《后汉书知意》。”可见《后汉书知意》是在他读《后汉书》之后所作札记的基础上加工而成。
关于撰写《后汉书知意》的原因,刘咸炘指出:“昔人评议范书者少于马、班,采掇简易,未旬而成,体例悉如前二书,其稍异者,间有论事语,以东汉史势人多不详也。然亦取足与书法相发明,不滥入史断语。马、班体例之精,不容议矣,范则多失,故今之所说,兼有纠弹,然仍名之曰知意者,读史终应恕作者之用心也。”即史家评议范书少于马、班,且后人对东汉历史研究大都不是很详尽,范书体例多失,刘咸炘通过对其优点和篇体不足之处进行分析,以探究史意,使得读史之人应该明白史家本来的用意。并指出后代史者对于范书也有众多误读,“然审今范书传本,则其破碎谬误又有非蔚宗之本然者”,因而“今故具论之,亦使蔚宗功罪明白也”。
《后汉书知意》在体例上首先对《后汉书》的篇体和识旨进行探讨及评价,然后在内容上有关《后汉书》中“本纪”和“列传”的各个篇章都进行了探究。
(一)篇体之失
刘咸炘非常重视明确史体,“书之款式,似不重要,而实重要,于史尤甚”,认为范书在史体上和马、班相比确有所不足,“盖综合之识亡而史篇失其圆神变化之体,变化之体失而结构散碎,史传乃成告身、行状矣。告身、行状之式始于范蔚宗,而后史皆沿之”。并指出范书篇体之失处在于如章学诚所论“范史列传之体,人自为篇,篇各为论,全失马、班合传师法”,且“其传中之论多止论一二人,即附其人事后,虽父子亦以论间断之,一篇之中遂分数传,盖其每篇本无一贯之处,每段各自孤立,甚至合传有全无意义,但以官位大小约略相等而遂合之者,此马、班所无也”。即范书各传孤立并不连贯,合传也仅以官位大小基本相同来分类,篇体上失却了马、班“圆神”之意。
对于《任李万邳刘耿列传》,刘咸炘认为“蔚宗书每人一段,间以论赞,而以事为纲之意渐失,如此传必分为六段,亦乏镕铸。若以任光、邳彤、耿纯为主而李忠、万修附,任光、刘植附耿纯,综叙河北之事,岂不省而圆邪”?对于《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刘咸炘认为此篇合传无义,“蔚宗之失又在不立表,若有表,则万修、刘植、景丹、杜茂诸人子姓传爵归之于表,名则附见他传中,何至繁文之娓娓乎?不知以事为纲,而斤斤于备一人之始末,后史之弊,自蔚宗开之”。即刘咸炘强调列传应以记事为纲,而非记人为主,合传、独传都皆如此,列传不应分合、独,也不应有正、附之分。
对于《班梁列传》,刘咸炘认为梁慬有战功,但无将略,不当与班超合传,“若省别立传而叙其事于《超传》末,下接勇事,以慬后攻羌之事别附篇末,则浑成矣。范氏列传皆各自孤立,故不能如是也”。刘咸炘明确地指出班梁合传的不当之处,“颇中要害,非肆意诋诃者可比”。
刘咸炘认为“汇传者,本以叙一事之源流,非止述十数人之事”,对于《儒林列传》,刘氏指出:“以今观之,所述东京授受仅有古学,盖以补《前书》,既非周备,亦嫌隔绝。若总述家法授受于前,具举名家,然后著之曰某自有传,乃以次述诸人事,略仿《*锢传》法,则贯串尤明,中间诸传不致漫无统纪矣”,而且“彼诸篇仅举其尤,不以非尤者入之也。然*、伦及召驯、杨仁止曾学经,而非名家,既无著述,亦未授徒,即在《儒林》亦滥,盖后史列传人人求备,以事少者归汇传之病,蔚宗已开之矣”。即对范书中列传每人为段,数段为篇的“花名印册”似体例,刘咸炘一语中的指出其不妥之处。
对于历代学者关于《后汉书》论、赞的争议,刘咸炘既批驳刘知几“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和赵翼“范书之赞则非为此,但于既论之后,又将论词排比作韵语耳,岂不辞费乎”的观点。对王先谦为范晔辩解,即“赞体用诗,以代序述,亦班、马之遗范,第范见刑时,书未大成,以赞继论,原未必范意如此”的看法也提出异议,指出“此说之疏谬,甚易见也。赞代序述,当如马、班,总在一篇,今其失正在不同马、班之遗范耳”。同时刘咸炘认为《后汉书》论、赞虽然在篇体上不如马、班,但也有其可取之处,“然则蔚宗加赞于论后,虽成赘文,而适以自护其书,无用而反有用也”。
(二)识旨之精
“既明体例,然后可求其宗旨。古史家皆有宗旨,非徒记事而已”。刘咸炘读史最重“史旨”,认为《后汉书》虽然在篇体上失却了“圆神之本体”,但是“尚有宗旨”。范晔在《狱中与甥侄书》中谈论到《后汉书》的史旨:“本未关史书,*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为举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刘咸炘对此予以肯定:“以今观之,其挥斥前人,诚为逾量,而自称之语,则非过夸,本意为论文,故惟自负其论赞之奇,其称许论赞皆是甘苦之言”,并且高度评价到:“当时之文,非弱即滞,不能健举,以范论较之,诚为纵放,不可以赵宋以后文势为衡。且蔚宗之文,远绍士衡,近越稚川,在八代中本为巨擘,唐、宋以后之轻诋,固无伤也。”
同时刘咸炘将范、班之史论风格进行了对比,指出两者各为其妙,“然蔚宗书体虽破碎方板,而序论则诚精,即不以文论而以史论,亦不愧体大思精之目。盖班氏赞语含蓄,不极议论,史家高度远致固应如是,蔚宗以为于理无得,自是误衡,而自作矫之,更为详畅,则别成其妙,与班相竞,然亦约其词句,以见裁味,非如宋后史断之恣为支辨,竟成子篇也”。并称赞范论“其美乃在汇传能挈举一代之得失,杂传能间破一时之习见,深观东京史势者自能知其精意深旨,非可一一举也”。
对于《后汉书》的史论,王鸣盛极其推崇:“蔚宗表死节,褒正直,而叙杀身成仁之为美也。诸传中亦往往见重仁义、贵守节之意蔚宗之表扬节义、推奖儒术如此”,刘咸炘认为王氏所举明矣,“范氏当士习骩靡之际,故颇取狂狷蔚宗于《樊英》《儒林》《独行》《逸民》诸传叙论虽并述得失,而终许其执义正俗之功,他如《来歙》《耿恭》《卢植》诸传,言及节义皆颇慷慨,即论以言已若是,其叙事之抑扬去取,尤不可胜举也”。并明确肯定了《后汉书》开创的激扬性史论风格对后世史书撰写的极大影响,“自光武推崇节士,变西京贪懦之风为廉直之俗,末流之弊,曹氏矫以尚功,魏末又矫以尚达,加之操、懿而后,篡夺相承,士既习于柔骨,史家亦囿于时俗,华峤乃华歆之孙,陈寿实谯周之徒,言论风旨,不能激扬,蔚宗崛兴,乃克振拔,自后刘知几辨举曲直,而史义始明,北宋诸公抗志力行,而士节始立,推溯其原,蔚宗实有中兴开启之功矣”。
二、对《后汉书》研究之辨驳
《后汉书》是我国的重要典籍,是研究东汉历史的重要史料,作为“前四史”之一,“从刘宋时期到清朝末年,对《后汉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训诂、史实考据、补遗辑佚等方面”。对于历代对《后汉书》的研究状况,刘咸炘并非注重文字和文义的考证,而是博采众家,引证丰富,从史法和史识的角度来对前人关于《后汉书》的研究进行史学批评。
(一)从史法角度探史意
刘咸炘认为“史之质有三:其事、其文、其义。而后之治史者止二法:曰考证,曰评论。考其事、考其文者为校注,论其事、论其文为评点,独说其义者阙焉”。这表明“刘咸炘治史的重点既不在于历史考证,也不是一般的历史评论和文章点评,而是要以探讨史意作为他史学批评的兴趣与重心”。在其《后汉书知意》的史学批评中也多处体现了他的这一原则。
关于《后汉书》中立“传”的标准,刘咸炘议论较多。对于《张曹郑列传》,李慈铭认为范氏将先郑、马季长的传书于康成之后,“时代失次,非也”。刘氏批驳此为妄说,“以官仕时代为据,是直视史传为官品齿録,亦陋甚矣。此篇为礼学,非徒经学名儒也。张纯、曹褒皆东京定礼之人,合传康成者,以郑学在礼,惜其未定礼也。史传叙人,不依人品高下”。王鸣盛认为自康成外,何修、服虔、许慎应皆入《儒林》,不升列传。刘氏也不赞同此看法,指出“古史列传原不以官位分合,无所谓跻,散传、汇传本无高下,范特为汉礼立此篇,故不入《儒林》,即入《儒林》,亦岂遂卑?王氏不通史法而好佞郑,故有此陋语”。从中可见刘咸炘主张立传应以事为主,既不以人品高下,也不以官位分合为标准。
对于《周*徐姜申屠列传》,李慈铭认为史传次序总以时代为民,此卷除周燮外都是汉末人,周、姜、申屠可入《逸民》,*宪、徐犀可入《独行》。刘氏指出“按史传类叙之篇从其 人之时代,《太史公书》已然,李氏说不足辨。既知蔚宗特立此数人,又疑其可入《逸民》《独行》,盖未尽知特立之意”。又对于范书将皇甫嵩、朱俊列传于《董卓传》之前,王补云:“传董卓而先以嵩、俊,其范史微意所在乎”。而*山认为嵩、俊以功名终,范史传二人于卓前不妥,“本以著臣道之终而启逆节诸臣也”。刘咸炘指出“按王说得范本意。勿论嵩、俊义当如何,要之当时事势,嵩、俊破*巾而不能制卓,汉之兴亡系焉,此传固当与《卓传》相接,*氏所辨有理,而谓著臣道之终,则非史意”。即刘氏强调读史应该探究范史本来的用意,而不能以己意猜度古人,“以己意曲说古书者,自以为知古人,而实不知也”。
对于《酷吏列传》,何焯认为董宣、何并之流不当列之《酷吏》,李章亦惟诛杀过滥,而范首及此三人,是由于“建武吏事深刻,上好下甚”。刘咸炘批驳到:“酷吏者,武健严厉之吏也,非专苛刻好杀之名也。故其中自分是非,后人乃多误认,此序、论著酷吏之所由始甚明,直可作马、班书解而释后人之惑。马、班书《酷吏传》之郅都,此篇之董宣、阳球,论者多以为不当入,皆闇论也。两汉皆多豪猾,此传不为建武一朝,何氏之言无一是者”。即刘咸炘从史识角度指出何氏的谬误。
(二)察变观风重源流
刘咸炘认为史学即是人事学,重在关系的综合,不能仅就事发论,还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