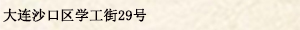散文人生是一次荒凉的行走
人生是一次荒凉的行走
文/白小白
序
作协会后第二天,我的公公——我丈夫的父亲去世了。然医院。本来只想做一个很小的白内障手术,却查出了糖尿病。术后恢复奇慢,医院里,等待伤口在我们看不到的世界里,挣扎着愈合。母亲自从嫁过来就一直住在我家的老房子里,后来老房子拆掉了建了现在的新居,母亲都没有离开过家,这样长久的住院从未有过。因此,她的情绪很有些悲观,常常莫名生气和发火。这很影响我的情绪。我每天都要故作随意地与她笑闹,告诉她糖尿病是怎样一种好玩的常见疾病。却不能宽她的心,她还是跟我抵触,甚至开始讨厌起我来。在我成长的三十多年里,母亲一直都是疼爱着我的,我长大后,母亲一直相信着我,以我为依赖,我想我已经习惯了她的依赖与信任,她的怨责于我,是个沉重的负担。姐们不能接受母亲被查出糖尿病这个事实,大家都觉得母亲这样老老的人,糖尿病患了就患了,不知就里地过完剩余人生,至少每一天都是快乐的。可如今被查出来,就成了一种沉重的心理负担,仿佛母亲害病不是可怕的事,真正可怖的倒是我们知道她害了病。我无法一一在电话里耐心解说,常常就恶了她们,再面对母亲,就少了耐心,母亲因此悄悄掉眼泪,这使我陷入更深的纠结。
在医院的所有日子,我的心绪都是恶劣的,低沉的,灰暗的,有一阵甚至听任自己的心绪落入宿命的哀怨。母亲病房右转是眼科的手术室,手术室门口通常都会坐着一些焦急的家属,穿过那些家属,一直向南走,是一排新装的病室。空空的走廊里,镶了两排木条钉成的长椅。这条安静的走廊,这些凉意沉沉的长椅,仿佛一个安静的魔咒,吸引着我。我在靠门的长椅上躺下来,让新木条的凉意从后背爬上来,穿透自己。这时候,我的脑子里像放映老电影一样播出很多过往,或者情不自禁地想一些心事,它们拥塞在我的脑子里,杂乱无序,纷纷扰扰。所有这些纷扰, 都会幻化成一双眼睛,那双眼睛眼神绝望疼痛,却有着颓废安静。这双眼睛后来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境里,让我的心不能安宁。这是我公公的眼睛。每到这时,我的内心,都会泛起落水的悲伤,我象一条溺水的鱼,张开腮,却发现自己不能呼吸。
那些日子,只要有空,我就会尝试整理自己,但我发现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我强迫自己安静下来,我让我自己蹲在岁月的小屋里,倒出所有,让所有的纷扰渐次离去,直到我可以提笔,写一篇素净的文字。为我可怜可敬的公公和婆婆。为了小缘和我自己。
一
公公突然去世了。接到丧信的时候,我正在三角龙湾的门口。天气很热,我和朋友们挤在门口右手边的小摊前面,热闹地观看品评商品,一面等着司机停车。6月份是三角龙湾的旅游旺季,停车场里大大小小地停着各色各样的车,景点里面是各色各样的游客。太阳好着,我们几个女生将伞撑开。电话是撑伞的时候响起来的。小缘在电话那端慌张地说话。他说,你回来吧。再说,你快点回来。然后又说,你马上回来。
太阳当头砸下来,砸出很重的声响。夫妻了十几二十年,小缘这样的慌张,我只见过两次,一次是婆婆去世的时候,正是清晨,我在当做我宿舍的办公室里上网。披发,素面,赤足,穿一件家常短裙。小缘在电话里哭腔地说婆婆没了,我的头轰的一下失去清醒,找不到合适的裤子。这一次,他如此慌张,我的心,跟着缩紧,再缩紧。太阳很热,热得让人失去方向。
我告诉我的朋友,家里有点小事情。然后安排了他们的行程。然后返程。
坐在出租车里,仍然辩不清方向,走了十几年的路,突然变得陌生而漫长,我想在 时间飞到小缘身边,将他抱在怀里。除此,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给他安慰。小缘还算镇定,告诉我,不要急,找好了车在等我们。
然而我还是不能不思绪浮沉,顾不上礼貌地应对司机。我的思绪,一忽儿滑向公公比较不老的时候,一忽儿又回到他的凄伤晚年。窗外的太阳,隔着出租车的玻璃,照在我的脸和其它裸露着的皮肤上,刺得生疼。
小缘是真的长大了,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还能够保持镇静,安排事情有条不紊,细致严谨。我们没有告诉开车送我们的朋友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路上,小缘都在与他们聊天。而我的思绪乱飞,完全失去了时间的概念和秩序,想公公的凄伤晚年,自责得心痛如割。
才发现,亲情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结婚初,我与小缘的家人,客气地相处,觉得此生都不会与他们有太深的感情纠葛,可是十几年过来,我发现我早已深深地爱上了他们。婆婆去世,我好几年不能从悲伤中拔出来;公公生前,我并不与他相处很近,可是他去世了,我再次痛得失去方向。人的感情,真是的一件奇妙的事情,感情的是由什么生成的呢?它在人的身体里吗?在哪一个位置存在着?它以怎样的方式存在?那么生命是什么呢?萨特说,生命是存在。如果生命仅仅是一个存在,那么思想呢?思想存在于这个存在的哪里?感情呢?感情存在于存在的哪里?
我们到家的时候,灵棚还没有搭好,公公睡在狭窄的走廊内的水晶棺里。于他而言,时间此刻是静止的了。他安静地睡着,完全失去了晚年的躁动, 能够显示时间的,是他的水晶棺上不时跳动着的红亮的数字,那些数字用以显示棺材里的温度、湿度和用电量。这些数字在他的生前,并不与他有关,不只这些数字,再多的数字,再多的世事纷繁,又与他有多少关联?而此刻,那些纷繁,更是远在他的尘世之外了。他的尘世,只剩了这几个数字,这几个明灭的红点。
这世界真有灵*存在么?如果有,那么我的公公,他此刻在做什么?他在他的躯体里么?可是,这个躺在棺材里的瘦削的老头,实在不是我认识的老人啊。他那么安静那么无怨无忧无愤地躺着,完全不是了他生前的模样。所以我想,他一定就在附近,在一个可以看到整个院落的地方蹲着,微笑地看着这一切,看着他的头上,一伙又一伙的人,哭着来,哭着去。
三年前,也是这样的光景,我和小缘在婆婆的灵床前,揭开她的面纸,细细地看她 的容颜,将她冰凉粗硬的手指握在我们的手里,与她告别。而在今次,我们只能隔着冰凉的玻璃罩子,看一眼再看一眼这个老人,止不住失声痛哭。小缘疼惜地将我拥在怀里,他知我身体太弱,不舍我多哭,而我的泪,失去了约束,在脸上,恣意地流。
小缘说:我没了母亲,就没了家,没了父亲,就没了根,我只有你一个最亲的人了。这话说得我肝肠寸断,下午的时候,就病倒了。我的思维曾有一度混乱,乱乱地晕着,年轻的赤脚医生为我做了简单的检查,血压正常,脉搏正常,那么到底哪里不正常呢?我知道我哪里不正常。我的疼,在骨子里,在灵*深处,在看不见的地方,疯狂地长。
公公的灵是傍晚的时候挪到院子里的,上面搭了高高的灵棚。彩色的灵幡挂起来,长长地拖到地上,无风而轻轻地舞。这总让我错觉公公的离去是快乐的。佛说,一世一个轮回,佛说生命的过程,是一次尘世的历练与劫数。那么,公公是劫满而去,脱了这一个皮囊之相的约束,进入了精神的自由么?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可悲伤的?我们这些后辈,实在应该为之欢欣和鼓舞。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愚蠢地悲伤着?我们凡俗的脸上,满溢着悲伤;我们的心里,拥塞着凡俗的欲求。
灵棚的左边,堆满着各色各样的纸活烛马,公公的马是鲜艳的红色,很高大很威武很鲜活,很象一匹真正的马。公公还有两个佣人,一个叫随手,一个叫得用,他们都被安排陪在马的身边,公公需要出行的时候,他们就来服务,一个用来牵马,一个用来伏在马前,当上马凳。纸活做得好,这两个小人活灵活现,身形虽不及常人的一半大,眉眼却鲜活得象个真人,这使我情不自禁地看着他们想,这是谁家的孩子?
我们总是对生活充满着希望,对生命充满着热爱,我们总是希望日子越来越富裕,直到过上前呼后拥的贵族生活,既然这一世里不能够,那么,就让我们寄希望于来生吧。于是死去的人,我们总要竭尽所能地为他们安排妥当。电视,冰箱,洗衣机,甚至电脑,一应电器,应有尽有。而公公是不会玩电脑的,冰箱和洗衣机会不会用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想,这些物什,公公最喜欢的,应该还是这匹高大的马,会不会连同这两个小人一并喜欢我不知道,因为公公既然成了佛,那么这两个小人,会不会一并成为佛前的童子?佛说,众生平等。公公会不会在喜怒尽去之后,将他们的生命交还给他们自己?
吹鼓班是*昏来的,他们沐着那天的夕阳,踏着轻快的步子,满脸肃穆的表情,在院子的一角安置家伙。有两只唢呐,一把二胡,一把胡板,居然还有一把弦子。我从未见过民间的鼓乐班里有弦子,因为它的调子在嘹亮张扬的唢呐声里,实在低沉,实在小声小气,实在不宜用来张扬丧家的明亮的悲伤。可是这个鼓乐班,他们竟然有一把弦子。我就十分地
二
公公的晚年生活,都是围绕着一件事情进行的。他想给自己找个老伴。这想法,从婆婆去世不到一百天的时候就有了。一百天,在当地农村,是一个标尺。一百天之内,叫做尸骨未寒。年近七十的公公,在婆婆刚刚去世的时候提出这想法,让儿女们有些心寒,所以,他的想法遭到了普遍反对。不仅反对,儿女们甚至不好意思在外人面前提起。
但公公对这事的热情与坚持远远超过了儿女们的想象。他先是给自己买了一些他认为穿起来很帅的衣服——硬领子的衬衫,需要系腰带的短裤,皮鞋。我们之所以注意到他刻意这样装扮自己,是他固执地拒绝我们买给他的纯棉宽圆领口的T恤、细松紧带的宽松大短裤和棉布鞋。然后我们又发现了他的另一个秘密:他在偷偷地吃一些提高性能力的药。这个发现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他的尊敬。我们害怕他胡乱吃药吃坏了身体,劝阻他又觉得无法启齿。春节的时候我回去看他,他的炕上并排放着两个被筒,我随口问跟在我和小缘身后的孩子:炕上怎么两个被子啊,谁陪爷爷住呢?孩子们没回答,公公的脸噌地红了。
子女们不再登他的门。儿子们是因为生气,媳妇们是因为不便。但我还是冒着大不讳跟家人提议,我说,要不,我们给他娶个老伴吧?包括小缘在内的全家人,以无限时长的沉默回答了我。大家觉得,公公不是疯了,就是花了。花了,在农村的语言辞典中,是花痴的意思,花痴这个词的解释,也不是一种病,而是有着被人嘲笑的含义。公公的想法成了家族秘密,大家理所当然地对外人守口如瓶,即使是家庭聚会,也没有人提起。
公公为此陷入了相当尴尬的境地。当一个隐秘的话题被传得久了,就会渐渐转为公开。当一个隐秘话题在家族内公开传播,传到外面去就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事实上,旁观者清这句话,用在乡间话题的传播上,最合适不过。公公的有悖于常情的举动,早已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他们说公公是一个老骚包,没正事,越老人越花。他们甚至还举出了许多例子,比如年轻的时候,公公曾跟谁开过玩笑,曾跟哪个邻居女人有说有笑,甚至还说公公跟儿媳妇住一个屋的时候,眼睛总往北炕的儿媳妇身上瞄。眉越描越黑,事越传越真,公公相处了一辈子的老邻居们,仿佛在一夜间认清了一个事实——表面憨厚老实的公公,原来竟是一个隐藏很深的色*。这使他要好的邻居韩婶不敢再接受他的友谊,别的邻居老太太走路也要绕着他,侧眼斜着他,老头们当然也不耻于与一个道德败坏的色*来往。这使公公完全陷入了可怕的孤立中。孤独与不被理解的痛,像一条可怕的*蛇,在极短的时间内,飞速地啃噬了公公的健康。
他的身体迅速衰老了。我刚嫁进这个家庭的时候,公公57岁,一餐能吃13个勺子大的粘火勺、一碗米饭、两碗菜、半块豆腐。如果换成面条,他会一个人吃掉半盆,盛出来放在碗里,那就是满满七大碗。他那时还能去两百米外的公共水井挑水。婆婆的厨房里有一口盛四担水的大缸,公公每次挑满这口大缸,都要从家到水井来往四次。公公家的院子是一面陡坡。公公稳稳地从坡上走下去,穿过门前横着的公路,再下一个更陡的斜坡,就到了水井。他把水桶放在扁担钩上,用木制的扁担一桶一桶打出两桶水来,担在肩上,步履平稳地步上两个陡坡,从容把四十斤一桶的水倒进缸里。有时儿子们回家赶上老人挑水,都会抢过扁担,但谁都不能一次把缸挑满。儿子气喘吁吁地坐在婆婆的炕沿上休息,他又不声不响地出去,把水缸挑满,然后脸不红气不喘地进屋坐下。婆婆在世的时候,公公一直保持着好饭量和挑水习惯。但婆婆去世不到两年,他的饭量锐减,挑水成了负担。他先把白洋瓦(一种很薄的铁片)水桶换成了塑料桶,然后又把满桶换成了半桶。他的水缸再没满过。枣红色的泥缸,上半部分因为终年沾不到水,泛着粗糙的不整齐的白圈。
再半年后,他连门也不怎么出了,不再每天坚持去一百米外的二哥家吃三餐,更不去任何一个儿子的地里帮忙,他把自己困在家里, 的工作是看电视, 的吃食是面条。婆婆的好厨艺,使公公养成了饭来张口的习惯,他一生只会做一种饭,就是煮现成的挂面。他把这种厨艺进行了演绎,就是在挂面里加上一包方便面,用方便面的调味包调和挂面的寡淡。公公的晚年是在大哥家度过的。善良的大嫂不忍心他过这种自闭生活,想了很多办法才说服他住进了大哥家的西屋。大哥的五间房子里住着大哥和他的儿子一家,现在又住进了公公。但搬过来后他的生活在本质上其实没有一点改变。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早上全家人吃饭的时候他还没有起床,半上午的时候爬起来吃一顿面条,然后看电视,看到饿了,再吃一顿面条,然后再看,直看到第二天凌晨,所有频道的电视剧都播放完了才去睡觉。
孤独对他的心理健康进行了彻底的摧毁。我想公公是想表达他的孤独的,有时他会评论电视剧里面的人物,可这时他又总是激动的,激动使他声音失真,表述不清,愤怒或流泪。我们尽量让自己的倾听更耐心更能鼓励他说话。但他还是渐渐失去了表达。他整日不说一句话,再后来干脆表述不清,及至放弃语言功能。社会和家庭的孤立使他的内心越来越孤独,越来越失去对包括儿女在内的身边人的信任。他对儿女说谎,拒绝劳动,种种行为都说明他对生命的存在不再珍惜,对生活心灰意懒。 ,他干脆放弃了尊严。在与儿媳妇和孙媳妇同住的 半年,公公对自己的生活没有进行一点整理,他的身体和尊严,都像决堤的水,溃不成*。他不喝水,只喝雪碧;不吃媳妇做的饭,只吃自己在房间里用电饭锅煮的面条;不吃桌上的菜,只吃小卖店里买来的新鲜和不新鲜的熟猪头肉。有时就吃坏了肚子,他就把脏裤子挂在门外的篱笆上。大嫂默不作声地拿去洗净晾干给他送回来,他理所当然地接过来,一个表示谢意的眼神都没有。他在屋里放了夜壶,白天在屋里撒尿。有次孙媳妇去请他吃饭,一眼撞上他白屁股对着半开的门,公公回过头看着孙媳妇嘿嘿地笑,脸上没有一丝羞惭。他已经不在乎成为全家最讨嫌的人。他完全关闭了与外界的联系,直到去世,没有与任何人做过交流,更不要说一次长谈。
三
公公是个有文化的人。我刚嫁进门的时候,家里有一本《虾球传》和一本《封神演义》。我很诧异在这个纯粹的农耕之家会有这两本书。后来我才知道,不只这两本,我的公公,年轻的时候,读完了《岳飞传》、《三国演义》等许多书。公公早年读过私塾。公公的父亲,我的爷公公是县屠宰厂的工人,公公是他 的儿子,他让公公读了私塾但没有读完,没读完的原因不是公公不爱读书,而是爷公公换了三房妻子。
小缘家族有媳妇早夭的传统。我的爷公公兄弟三个,媳妇都没有活到五十岁。我爷公公一生娶过三个妻子,个个都活了不久, 一个也没有活到六十岁。我爷公公自己活到八十多岁,剩下的近三十年的岁月,都是他一个人度过的。我刚嫁过去的时候,爷公公还活着,他穿一身旧式的黑色衣裤,里面罩一件白色家织布汗衫,黑色布鞋,终年戴一顶宽沿礼帽,拄着一个光洁的木质拐杖。眼神坚定而慈祥,慈祥得看不出他曾经当过屠夫。
爷公公是个怪僻的老人,他的好恶都非常鲜明。他不喜欢自己的独生儿子。因为不喜欢,拒绝给儿子娶媳妇。公公失去了母亲就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长到17岁了,还没订亲。可别人在这年龄都已做了爸爸,后来公公的大伯做主,给公公娶了我婆婆。婆婆比公公年长两岁,做一手好活计,却不识字。公公与婆婆无法交流,一生没有爱过妻子。他们的交流仅限于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一般的小事,难以达成一致的大事,通过思想沟通,不如通过拳脚来得直接和便捷。婆婆没文化,也不懂得爱情,她不计较丈夫爱不爱自己,她所有的人生目标都停留在如何保证生存上。因此她一生做得最多的功课,是忽略别人的忽视和取得别人的重视。她在嫁给公公的最初时间里,成功忽略了公公的冷漠和拳脚,后来她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占据了家庭的主导地位,成为家里的实权派。
公公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有志向的人,他曾做过柳河县机砖场工人,后来回到农村做过生产队里的生产队长、记工员。年轻的公公是个帅小伙,一米八三的个头,腰直板,国字脸,力气惊人。在机砖场,没有人能超过他的产量,月月都是 。北方的机砖场都是一个模式,就是用粘土在机器上做成土坯,然后把土坯放到四面通风的遮阳棚里阴干,干至四成的时候,上下倒一遍,把上面的倒下去,下面的倒上来,干至六成再倒一遍,干到八成倒第三遍,然后把十成干的土坏放进窑里锻烧。机砖烧好之后,再从窑里运出来,这个活,叫“出窑”。现在机砖场用机器出窑,但那时只能用人工。“出窑”是机砖场里最苦最累的活。窑刚打开,里面的热气还没散尽,出窑的工人,大冬天穿着单衣单裤还热得汗流浃背,呛人的砖末粉尘,被脸上的汗水冲成道道。工人把机砖码到担子上,用扁担挑出来。一担砖一百斤。窑门小,只能容下一个人出入,干这项工作的工人必须分头干,各在各的窑门里干活。一个工人一次挑一担,公公力气大,双肩各挑一担砖,还比别人走得快。因此他总是干两个人的活,赚双份工钱。
这样的辉煌没持续多久。年的饥荒像一张巨大的灰网覆盖了城市和乡村。公公的第二个孩子刚刚出生不久,几个月的孩子无法消化粗硬的代食。机砖场的定量口粮,无法填饱饭量超大的公公的胃。婆婆吃不饱没有奶水,城里的水泥地里长不出可以喂养孩子的地瓜和土豆,这个孩子终于有天停止了微弱的呼吸。小孩子的死让婆婆褪去了初嫁时的羞涩和温顺, 次焕发出抗争的力量,回农村去!到可以养活孩子的土地上去!公公 次听从婆婆,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辞掉工作回到农村当了农民。农村的广袤土地上的野菜和树皮成全了公公一家的胃,也成全了婆婆的家庭地位。婆婆的巧手厨艺在饥荒倾覆的农村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一样的野菜和树皮,到了婆婆的餐桌上,魔术般地变成可口的大餐;同样多的粮食,在婆婆的手里,能让家人吃得更长久更可口;同一种代食,婆婆能变换出许多花样。榆树皮做的粉条,婆婆可以做得又细又长又滑又软。一碗玉米面加上一筐地软皮,就煮出了一锅可口的汤面。凭借着这个能耐,婆婆很快成为同村媳妇的 。媳妇们看着婆婆的餐桌翻新自己的手艺,这使婆婆空前地找到自信,意气风发。饥荒过去后,她的 地位已经牢不可撼。这种 气质后来跟随了婆婆的一生,直接了当地在家里得到发挥,婆婆从顺从到参*到当*仅仅用了几年时间,知书达礼性格耿直的公公骨子里的性格其实是温顺的,他实现从听从妻子的建议到完全放弃家庭主导地位这个转变,也只用了几年时间。
让公公完全失去主导地位的是“养牛事件”。农村第二次土地改革实行单干的时候,公公跟村里 批有志向发展蓄牧业的农民一起,从内蒙古运进一批改良牛。柳河县砬门乡的 头西门达尔优良种牛就是公公当年引进的。但是公公的*牛养殖事业并不顺利,他们引进的草原牛不适应东北的气候,加上缺乏养殖技术,他们的牛一个接一个地死掉。眼看着生意赔钱,合伙人纷纷退股,七个合伙人退了六个,耿直的公公一个人承担了所有债务。巨大的债务,即使是倾家荡产也还不起,公公只能以各种方式延缓还债日期,慢慢偿还。此后很多年,公公的全部精力都用来挣钱还债。经济拮据使他张不开手脚,生意失败摧毁了他的自信。失败的阴影,一直笼罩着这个家庭,成为公公心中的块垒。小缘是公公最小的儿子,我嫁进家门的时候,二哥的牛刚被信用社牵去拍卖不久,还清了 一笔欠款。为此公公彻底失去了在儿子面前的尊严。
公公变成一个寡言的人,他和婆婆的交流都用吵架的方式完成。有时是两个人吵,但更多的时候,是婆婆一个人吵。如其说是吵,不如说是婆婆骂着发出指令,公公沉默着执行指令。婆婆的指令一个接一个发布,公公动作迟缓地一个一个完成。有时完成得好,婆婆以沉默的方式表示嘉许;有时完成得不好,婆婆以责骂的方式总结。每当这时,公公就会激动地辩解,但他的辩解无一例外地遭到更深重更激烈的责骂,然后他会更急切更激动的辩解。激动使公公的声音失真。公公的声音不是浑厚的那种,而是有些沙哑和尖锐。每一次争辩,都会让他面红耳赤青筋暴起。每一次争辩,他都用尽全身力气。婆婆很反感公公的全力争辩,这使她的声音从一开始就气急败坏地冲上高八度。这时争辩就变成了争吵。这种争吵通常都以双方的声带都承受不住极限摧残而不了了之。有时忍无可忍的公公选择施以拳脚辅助。吵架的副产品是婆婆的心永远是阴冷的,婆婆的脸上永远罩着厚厚一层严霜。一个家庭的实权派脸上总是挂着寒霜,这个家庭的气氛就总是阴冷的。副产品之二是公公的懈怠。他对生活和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持着懈怠的态度,他不用思考,只需凭着本能完成指令;他不必积极热情,因为他的任何一个决定都得不到婆婆的支持,而婆婆安排则必须完成,公公只能用懈怠对付他不喜欢的事情。我有时想,懈怠,其实是一件 毁灭性的武器,它比锐利的刀剑和思想更让人防不胜防,如同温水煮蛙,它让人在无知无觉中消磨自己。被消磨了的人尚不知情,其实已经失去了自己。公公和婆婆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他们双双老去。
我本能地反感着这种家庭模式,我不能理解婆婆那样对待丈夫,我同样不能理解公公的懈怠。我觉得这个家庭哪里出了问题,但我找不到症结所在。直到我和小缘一天天长大,长到不用爱情而是本能地采用家族习惯支撑我们自己的小家庭。我发现,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堕入了公公婆婆的家庭模式。婆婆一手带大的小缘,本能地不爱思考,永远不主动。家里的事情,不管大小,只要我不开口,坏了的包括水龙头和灯具的一切物品,永远得不到修理。可是只要我吩咐的事情,无论喜不喜欢,他都不会拒绝,更不会选择别的方法,他永远只用一种方法完成我的吩咐,那就是懈怠地对付着完成。他的懈怠使我恼火,他的不主动与不拒绝同样使我恼火。我尝试与他交流,但不管我采用什么方式,他都会觉得我在指责,他会立刻把自己武装起来,面红耳赤地跟我辩解。我像婆婆一样气急败坏地面对着他的辩解。我们像公婆一样毫无建设意义地争吵。疲惫不堪地不了了之。我尝试过与小缘进行有效沟通,我甚至用公公和婆婆的人生悲剧做为蓝本给他讲解,小缘深深认同我的观点,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可是,事到临头,他又会惯性地回归本性。在经过无数次沟通之后,我决定放弃努力。我发现,在性格深处,我们谁都无法让别人改变,夫妻间最能做的一件事是相互适应。我努力适应小缘的习惯,结果是我变得像婆婆一样唠叨和抱怨。有时,我会深深警醒,我怕有天,当我老去,我也像婆婆一样有着一份阴冷得无法暖起来的内心。
四
在传统苦戏里,最苦的人是小白菜:小白菜呀,地里*呀/三两岁呀,没了娘呀/跟着爹爹,好生过呀/就怕爹爹,娶后娘呀/娶了后娘,三年半呀/生个弟弟,比我亲呀/弟弟吃面,我喝汤呀/捧起碗呀,泪汪汪呀/亲娘呀,亲娘呀/亲娘想我,谁知道呀/我想亲娘,在梦中呀/桃花开过,杏花落呀/想起亲娘,一阵风呀。婆婆的的人生,比小白菜还要苦些。婆婆姓孙,三岁的时候,死了父亲,妈妈带着她改嫁到董家。继父家里有一个五岁的姐姐。姐姐是继父的前任妻子带来的孩子。姐姐比她命苦,跟着妈妈嫁到董家,不久母亲就死了,把五岁的她扔给了继父。三岁的孩子不懂 疾苦,妈妈改嫁对于婆婆的意义,就是多了一个五岁的姐姐。姐妹两个很快就建立了友谊。所以,死了父亲随娘改嫁这事对于婆婆没有造成 ,而是有些幸运。我有时想如果上苍没有安排后来的灾难,日子就这样过下去,那么婆婆就是一个幸福的女人了。
妈妈改嫁的第二年,家里多了一个弟弟。弟弟虎头虎脑活泼可爱地长到四岁。一个炎热的午后,弟弟在院子里欢快地没有方向地奔跑,全然不顾追在后面的暴烈父亲的怒吼,四岁的孩子还不能懂得父亲的怒吼对于他的潜在危险。父亲的怒吼反而助长了他的调皮,他像追赶太阳的夸父一样越跑越快,直到父亲手里的铁镐飞到他的后心上,他才像每一次奔跑不小心绊到了脚下的土块一样,扑倒在泥地上。不同的是,每次绊倒他都会哭着爬起来,而这一次,他安静地趴着,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也没能将他唤醒。
巨大的悲痛压倒了母亲,长期的家庭暴力早已让她身心憔悴,丧子之痛更是雪上加霜。母亲在这个夏天里走完了人生历程。可怜的婆婆失去了 的亲人。她只能跟异姓姐姐相依为命,别无选择地跟暴烈的继父共同生活。这一年,婆婆七岁,她的姐姐九岁。在乡间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最苦的苦戏莫过于继母如何折腾孩子,后父如何没有人性。婆婆的继父,我没有见过。我嫁过来的时候,他早已做古,关于他的所有传说,都源自婆婆或其他亲人的描述。在他们的叙述里,他是一个性格异常暴烈的男人,打老婆是家常便饭,包括我婆婆的母亲在内的三任妻子,都因家庭暴力而死。婆婆的母亲去世后,再没有人敢嫁给他了。带着两个小鸟一样战战兢兢的女孩一起生活,没有使他的暴烈有所收敛,他的拳脚经常落在女儿身上,挨骂和挨打,是婆婆姐妹两个每天必做的功课。婆婆在他身边生活的十二年,本应该是一个女孩 的花季,挨打受骂使婆婆对青春年少没有幸福的体会,十二年里到底受过多少打骂无法计数,但那些打骂在婆婆的身上留下的痕迹却也不甚清晰。看得见的痕迹只有两个。一是婆婆的手,在最冷的冬天不能受凉,一受凉就麻木。婆婆说,有一年冬天特别冷,婆婆跟着继父一起铡草,婆婆力气小压不动铡刀,只能跪在地上给铡刀里续草,她双手紧紧抓住一握稻草,继父每铡一次,她就把手里的草往前送上一寸。潮湿的稻草经过冰冻,上面结成了厚厚的霜,婆婆每抓一把,都像是抓在冰块上,一双手很快就冻僵了。可是婆婆不敢说手冷,她知道只要她一开口,继父就会把手边的东西披头盖脑地砸过来。现在,继父的手里是巨大的铡刀,她怕极了刀片上面凝霜的寒光。她机械地随着继父的起落动作一下一下续草。草铡完了,她的手却怎么也暖不过来。半个月后,她的两只手,像脱去手套一样脱去了一层硬皮。从此她的手就落下了怕冷的毛病。再是婆婆的左小腿上,有一个很深的坑,婆婆说,这个坑,是继父用镰刀背砍的。原因和背景全都忘了,总之继父当时正在用镰刀干活,镰刀飞过来,刀背正好砍在婆婆的左小腿上,异乎寻常的锐痛使婆婆立刻扑倒在地。婆婆说,也不见出血,就是疼,疼得扛不住,在炕上躺了两天。两天后支撑着下地干活,腿上就出了一个坑。婆婆不懂得为什么没出血还能这么疼,她不知道继父的刀背隔着皮肤把她的肌肉砍断了。
身体的伤痛可以恢复,心灵的创伤无法弥合,继父的暴虐给成长中的婆婆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痕。但婆婆至死也不知道继父对她的 到底有多大,因为她不知道自己的心理有隐疾,更不知道自己的心理扭曲给丈夫带来的毁灭性 ,给儿女们留下的悲剧隐患。
孩子的心灵是一张白纸,一旦被画上某种颜色,就绝少可能被修改。有些人天生就具有植物性,小孩子都是藤生植物。我曾在五女峰上见过一株藤,她从一棵被劈成两半的大树的树干中斜生出来,将根扎在树干上,可她长得枝繁叶茂,远远超过了被寄生的树。婆婆也是一株藤,在求得生存上,她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顽强毅力。跟继父生活的十二年,她不仅没有憔悴和凋零,反而出落得麻利刚烈,而且练就了一手非凡的好活计。除了好厨艺,婆婆还做得一手好针线,一个村子的人,结婚的喜被,装老的寿衣,都是请她来做。婆婆絮得一手好棉花,她絮的棉被不滚包,她絮的棉衣可以用水洗,怎样揉搓也不会出窟窿。婆婆的好活计使她在社会交际中获得了尊敬,很清晰地满足了她的存在感,这使她轻易地在生活中建立了自信。没有人知道这个心灵心巧的女人内心深处的情感缺失。
在婆婆的情感世界里,是没有爱情这两个字的。亲情或任何一种友爱都是给予、施舍或交换的。她常说的一句话是,谁谁对我很好啊,谁谁说他老想我了。她希望得到别人的重视。这种重视,在她看来,就是最重要的。重视等同于爱。她的施爱的方式,也是给予、施舍或交换的。她的爱,更像是一钵满溢的水,需要盛满,满得溢出来,淋到了人,她还要索回同等的石子填进去,以保持容积。但她的钵,从来就没满过。她的爱,是单薄和干瘪的,又磅礴丰沛得无法内敛。她无法给予丈夫丰富的爱。丈夫,是她的假想敌,她必须以任何一种可能的方式击败对手,牢牢占据着至高点,她必须比他重要,才能让自己的内心生出安全感。这使她对丈夫的态度又矛盾又纠结——一方面,她不管自己多么劳累,不管身体舒服不舒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不间断地精心做好丈夫的三餐。公公喜欢吃豆腐,婆婆就练就了各种豆腐菜的做法;公公喜欢喝一口,她就每餐都为公公倒上一杯,有时饭菜都准备好了,洗了手准备吃饭,却发现酒喝没了,这时不管多累,她都会贤惠地穿上鞋,拎着酒瓶出门打酒。这样做的时候,她像一个温顺的妻子,一根柔长的缠树的藤。可是另一方面,她又不能允许丈夫有自己的主权,她不害怕主权本身,而是不能允许对方比自己更强大,她要比对方重要,存在的重要。
婆婆的全部社会交际都局限在这一个焦点上,不管远亲还是近邻,只要对方跟她讲多么多么喜欢她,在她不在的日子里有多么想念她,她就会感动得无以复加,将对方引至亲的人。她常跟我讲,哪个亲戚对她好,给她买了衣服,想念了她,亲戚的小孩子亲了她的脸……每当说起这些,她的脸上,都洋溢着真诚和幸福的光辉。婆婆对小孩子的教育,也集中在这个焦点上。她自己生养了六个孩子,每个孩子都被无一例外地在潜意识里被灌输了这样的思想:母亲是最重要的人,父亲在家里可有可无。儿子教育了孙子。在我家里,每个孙子都知道,奶奶是家里 的女王,奶奶的权力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我刚嫁进门的时候,姐的孩子三岁,是个调皮好动的小孩。那时候,姐和她的孩子跟婆婆住在一起。有次小孩子好奇心起,撕掉了婆婆收集的一个塑料瓶子的包装花纸,婆婆大怒,猛丁抢下孩子手里的瓶子,一边大骂着披头盖脸打过来。小孩子被吓傻了,忘了哭泣,本能地举起胳膊挡脸,却不小心手指杵到了姥姥的眼睛。婆婆立刻歇斯底里,嘶着嗓子破口大骂:你还敢打我?你不怕雷劈死你?!可一旦小孩子听话,将她尊为女王,她又成为一个顶顶慈祥的老人。
小孩子的心性与狗相似。狗的眼睛是世界上最清澈的海。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只有情感纯洁的狗才能拥有那样让人心动的眼神。很多人喜欢养宠物狗都是被狗的眼神倾倒。有人推测,聪明的狗的智商,可以相当于三四岁的孩子。小孩子的心灵,像狗一样单纯而美好。他们信任和依赖大人。狗会看着主人的脸色决定跟不跟主人开玩笑。大人的脸色,是孩子成长的标尺和风向标。父母的情感表达方式,客观上引领着孩子的心灵成长,从而塑造孩子的品格。婆婆的六个孩子,性格不一,却无一例外地被安装了一些共同的特点:偏执,自私,自卫。成年以后,个个孩子都被这些特点或多或少损害了生活。受害最深的是刚。刚是大哥的儿子。刚同时遗传了父亲的偏执刚毅和母亲的浪漫与长情。刚本应成为一个真诚率性自然的孩子。但是做为长子长孙,刚受到了奶奶的最多疼爱,奶奶对他的教育,使他性格里的两股力量发生冲突,并且不可逆转地扭曲起来,青春期的时候迷失了方向,进过一次监狱。从监狱出来后,他没有变好,反而变坏了。家人把对他的 期望变成了 失望,彻底摧毁了他的 一点信心, 完全失去了人生航向,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是非判断完全扭曲纠结在一起。已经成年的他,要解开这些结,已经不可能了。
小缘也是深受其害的孩子。小缘是婆婆最小的儿子。他对母亲的情感依赖超过了我的想像。我被他的偏执和自私折磨得几近崩溃,有几次几乎就要放弃了,但每次小缘都用对母亲那样的依赖情绪征服了我。每看到他的眼神,我就会偃旗息鼓,乖乖就范。小缘绝望的眼神让我知道,他的内心有多么孤独和无助。小缘有时通达而宽厚,儒雅高贵得像一个天使,这样的时候,他会伸出长长的臂来,环我在怀里,对我说爱我。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完全相信他是真诚的,我还知道,此生,我都是他的 ,没有人能够取代我在他心中的位置。而在另一个时刻,或许就在一转身间,他儒雅的嘴里会吐出粗鲁而鄙俗的恶*语言,他歇斯底里骂人的样子,常常让我惊讶得措手不及。每个人的心灵里,都同时藏着两个人,一个是天使,一个是魔*。每个人的性格里都有优点和缺点,我们倾尽一生的力量,就是让自己每天成长,不断地修正自己,让优点更多,让缺点更少;让天使更大,让魔*更小。可是,我实在想不明白的是,小缘的魔*和天使,此消彼长,周而复始。我知道他每天都在努力,让天使打倒魔*,他自己纠结得很厉害,但他的内心,像一块吸水的海棉,让他的努力消弥无形。
五
成年后,儿女对父母的爱会越来越趋向理性,虽然这种理性还客观地被罩在家族性之内。但社会经验与生活磨砺让人对生活与生命进行反思,像老牛反刍一样,越来越嚼出理性的味道。婆婆的儿女们的反思结果是在情感上不再迷信她的主权。婆婆的晚年陷入深刻的孤独当中,她坚毅,独立,但缺少安全感。这让她对公公的感情发生了质的转变,她真切地依赖着公公,真诚地 婆婆去世后,儿女们才注意到公公的存在,大家仿佛一夜间长大了,珍惜起父亲的存在。一个家庭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父亲才是这棵大树的主根,只有他在,只有他将自己的根须深深地扎入泥土,才有了一家人的枝繁叶茂、血脉相连。我们已经失去了母亲,不能再失去父亲了。大家专门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认真研究了公公的赡养问题,还给公公存了不小的一笔零花钱。大家觉得,关于公公的晚年,已经做了最妥善的安排。但是公公一点不领情,婆婆的去世,他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悲痛,虽然他不会洗衣服不会做饭不会照料自己的生活,但他还是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希望与信心。他雄心勃勃地拒绝了二哥的邀请,二哥承诺,只要公公答应搬过去跟他住,他不用公公干活,不用公公的钱,由二嫂照料公公的饮食起居。可是公公据理力争, 勉强同意一天三顿饭走路去二哥家吃,但决不住在二哥家里。他整理了自己的老房子,甚至还整理了屋后的小片地,想要种一片玉米。不久他就张罗着要给自己娶个老伴。他的举动严重 了儿女们的感情。儿女们在婆婆去世后,原谅了她所有的缺点,并且不断回忆婆婆在世时的方便和美好。比如婆婆每年做的酱和咸菜,够每一个儿子家吃;比如婆婆在时,儿子们回家总能吃到母亲做的各种面食。这些记忆越是经过回忆的打磨,越是晶亮清新,痕迹清晰,就越是影响着公公娶老伴的可能,直到 成为完全不可能。
公公严重地衰老了。原来只有少数几根白发,现在仿佛一夜之间就白了一半。原来他只是话少,现在他如无必要,基本不怎么说话,行动迟缓,饭量锐减。他用沉默和不配合做为抗争,但他的抗争是多么微弱。医院里例行的体检中,仪器显示的结果永远是健康,但他现在飞速地老成了一棵枯朽的树,在一次进城吃饺子的时候轰然摔倒。他摔碎了髋骨,从此开始卧床。然后,在婆婆去世三年之后的一个上午,去世了。
像一棵大树失去了保持直立的主根,像一条大河失去了奔腾的主流,我们失去了父亲。儿女们在父亲去世的 刻,就原谅了他的所有不好,开始检讨自己的过失。可怜的公公,终于以最 的方式为自己争得了理解和尊重。但一切都太迟了啊。公公的葬礼按照乡间的丧俗被安排得隆重而热烈。葬礼严格按照程序一个节目一个节目往下进行。在给公公“送盘缠”的时候,大哥哭得死去活来。大哥被两个人架着,倒退着行走,哭得几乎昏死过去。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掩饰深刻的悲痛,真诚地悼念这个逝去的,我们 一位至亲的老人。“送盘缠”,是乡间丧俗当中众多程序中的一个。是出灵的前一天晚上,死者全家老小,和远近亲戚,披麻戴孝,顺着出灵的方向,走出村外,烧掉祭祀的所有香烛纸马、花圈烧纸,意思是给路上的小*送些纸钱,以买通死者的冥路,好让死者的*泉路走得从容顺当。公公是村里的大家庭的长者,是村里最老的老人,戴孝的白色的队伍,排出了一里地,几乎站满了整条街,队伍前面到了目的地,后面的人才离开家里不久,乐器班吹出了最哀伤的曲调,燃烧纸活的大火烧了半个小时那么久……公公享受了村里最隆重的葬礼。公公的葬礼受到同村老人的强烈羡慕,他们都说公公养了一群最孝顺的儿女。可是,这一切,都已与公公自己无关了。此刻,他安静地躺在水晶棺里,与他发生关联的,只有棺椁上面的那几个明灭的红点。程序严整,动作规范,场面热闹的隆重葬礼,更像是一场拉场戏,更像是儿女们的一个秀场。
我总觉得,公公没有走远,他一定还在现场,在某一个角落里,微笑着观看自己的葬礼,微笑地看着我们的悲伤或忏悔。生命是一场红尘的劫,现在,他劫数圆满,回归了自然,一切痛苦都不重要了,一切快乐也都不重要了。他有知有觉,亦无知无觉。公公,一定已经成了佛,看破了人世的爱恨嗔痴怨,并宽宥了我们的所有过失。可是,凡俗的我们,怎么都不能像公公一样豁达了然。我无法不为公公的人生悲伤和哭泣。人生是一次旅行,无爱的人生,是一次荒凉的行走。公公有没有爱过人,我不知道。但有没有人在他生前,爱过他呢?
六
人,是多么孤独的孩子。
(作者为辉南作协名誉主席)
北京哪个白癜风好白癜风哪治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