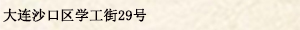收心斋
九九重阳日
深深敬老情
今日头条“外交官”退休后赴法国“补课”近日, “外交官”、年近八旬的恩高校友文隆胜出了一本新书叫《补课》。
该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详细记录了作者近两年在法国与女儿、外孙一起生活的家庭故事,字里行间洋溢着一名与家人”聚少离多”的外交官退休后终于补上“亲情”这一课的幸福与快乐。(文隆胜,长期从事文化外交和科技情报工作,19次公派出国,常驻、考察和访问的国家达18个)
此前10月8日,文隆胜曾回到家乡利川团堡,将自己数十年积攒下来的41件外国民俗纪念品和1万元现金捐给了团堡镇。
“这些年,虽然我走了那么多地方,但我的根在利川,*在利川,这片土地让我饱含深情。”捐赠现场,年近八旬的文隆胜向父老乡亲深深鞠躬。
文隆胜老校友小时候的故事
出生
茅坡口
年农历2月初,我的家乡鄂西山区,山上的积雪有的已变成了水,润湿了一片片坡地,屋檐上的冰钩越来越细,嘀嗒嘀嗒的水把疏松的地面琢成一个个小坑。中午时分的阳光多少带点暖意,大地开始苏醒,这预示着春天就要回来了。农户们跟往年一样,已开始准备春耕春播。
2月初3的凌晨,被高山遮住的天空还没有发白,文家就忙活开了。这天跟平常不一样,不是忙上坡干活,而是要迎接一个新生命的来临。山里人,医院,没有产房。家境好的,到附近请个接生婆。一般人家,都是自己接生。遇上怪胎难产,不是母死,就是子折。杜氏(林芝)大婶已生过3胎,习惯了,既不叫,也不喊,沉着地等待着又一个小生命的诞生。
不多时,“哇”地一声从屋里传出:“我们茅坡口又多了一个人。”他上面两个都是姐姐,哥哥两岁时就已离去,文家添了个胖乎乎的小子,喜出望外。消息像春风一般,很快传遍了左邻右舍,有的来祝贺,有的来道喜,忙得文家不亦乐乎。满月那天,文家还摆了酒席,请来了乡里知书识理的私塾先生,说是要给这个儿子取个好名字。教书先生可动了一番脑筋,既要符合辈分,又要有意义,更要讨得文家的欢欣。琢磨来琢磨去, 取名“隆盛”,隆是这代的辈分,盛乃昌盛,正中文家想发家致富的意。一拍即合,从此,这个名字就成了我朋友永远的代号。家里人和长辈亲戚们溺称“盛娃”。
年,农历戊寅,故我的朋友属虎。本来全国正值抗日烽火熊熊燃烧的时刻,可我家乡——鄂西这块僻静的山区。除了偶尔听说一些抗战的消息和看见天空飞机往来和听到它们的轰鸣声外,老百姓没有见过可恶的日本兵,更没有遭受被占区人民那般的苦难。文家火了两年,又种地,又做小买卖,虽说不算富裕,吃穿自然不成问题。然而,好景不长,我的朋友也只有面对残酷的现实,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成长了。
我的朋友比我大两个月零3天,我一直管他叫“盛哥”。请看他的自述吧!(腾龙)
图为刘少奇、周恩来接见出国艺术团
可怜的小白菜有一首歌谣在我们家乡流传很广,很多人都会唱,歌词大意是这样的:小白菜呀,遍地*呀,两三岁时死了娘啊;只好跟着爸爸过哟,又怕爸爸娶后娘哟……
这首歌我很小就会唱,不知是我姐姐教的,还是别人教的。因为这支歌唱起来顺口、凄凉、贴切,似乎是哪位专为我作的似的。
我的父亲叫文寿昌,又名文玉堂,经常使用的是后一名。他个子不高,勉强上了四年私塾,能认识自己的姓名,进行简单的心算。地方上不少人都知道他,他还当过几年甲长。他小时候很苦。我的祖父叫文德宣,既会种地,又会裁缝。但我祖父21岁那年,不知得了什么病,那个时候,山区特别落后,根本没有医疗条件,年纪轻轻地就离开了 。
祖母改嫁到孙家,我的继祖父也是既会种庄稼,又会缝衣服。听说,有一回他在山上砍柴,一失脚,滚了好远,成了瘸子,以后就只能全靠给人做衣服为生了。我的祖母跟继祖父给我生了几个叔叔和姑姑。我的父亲很早就脱离他们而独立生活了,一生种过地,卖过力,做过小买卖,起早贪黑,勤耙苦做,到我记事时,家庭生活已算可以的了,解放时还定为“中农”成分。然而,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压坏了腰,坐下就起不来,后来又得了肺结核,咳嗽不止,加之年大灾荒没饭吃,年仅52岁就丢下孩子们走了,永远地走了。
我的母亲是大丫口杜家的,离我家不太远。听人们说,我的母亲个子比较高,但裹了小脚,在地里只能跪着干活,为人善良、贤惠、勤俭。我两岁时,我的母亲突然得了病,病的时间不短,不知是什么病,总是不好,后来神经失常。一次,她要给我喂奶,我的大姐刚把我递到她手上,扑通一下,就把我扔到了地上,我哇哇直哭,好在是土地,我又胖,才没有受伤。
最悬的是有一回,她从我大姐的手里夺下我,抱着我就往猪圈底下跑,眼看她就要把我扔进粪堂。说时迟,那时快,我被闻讯赶来的父亲一把拽住,才没有扔进去。人们围上来,一个个目瞪口呆。我的母亲愤愤不平地辩解:“我就 了。我死了,他要受苦,不如把他淹死。”我们那里的粪坑很大很深,足有三、四米长,两、三米宽,一两米深,是积肥的主要来源,猪粪、人屎、烂菜、臭水都往里拥。那回要是把我扔进去,那我早就没命了。
从此以后,比我大8岁的梅芝姐,就背着我到处躲,四处藏,猪圈里、牛栏里、庄稼地里、山林里都曾躲藏过。后来,我的母亲折腾得不成人样,披头散发,家里人一个个也耗得精疲力尽。一天,趁我的父亲下地干活,她站在床头上悬梁自缢了,临终时,才30来岁。
别人问我,我妈妈死的时候,记不记得起。说来也真怪,那时我刚两岁,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堂屋里用两条高板凳放着一副黑色的棺材,一群道士敲锣打鼓,又唱又跳。有人要我磕头,我磕了,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还跑进跑出玩个不停。我懂什么呢?
从此,我就成了一棵可怜的“小白菜”。
我的母亲过世后,我的父亲忙里忙外,根本顾不上我们,实际是我的姐姐承担了母亲的义务,背我抱我,哄我睡觉、穿衣,给我洗洗弄弄,以后又给我补衣服,做鞋子。
嫁给李家的二姑与我们家同住一屋。她很喜欢我。她一放工回家
,我就伸出两只小手,“二给,二给”(叫不准二姑)地叫个不停,硬要她抱。
一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父亲认识了我后来的母亲。我的继母姓朱。听说是这样的:她嫁给山脚下刘家,丈夫不久就病逝了。一天,她上山来打猪草,被一伙人发现并议论开了。有人提亲,让我的父亲娶过来。很快,就成了。
我3岁左右有了后母。我的后母没有文化,不多言语,劳动却是把好手,割草耪地比谁都快。因为是后母,毕竟跟自己的妈妈不一样,不敢亲近,总有一段距离,心里话没处说。后来,她给我生了5个弟弟,有一个不到两岁就病死了,其余4个都长大当了农民。年,我的父亲去世时,最小的弟弟还不到3岁。
因为我自己没有感受到母爱,我的父亲又忙又严厉,很小我就立下自立的愿望。我曾对人说:“我长大了,找一块地,造一栋小巧玲珑的房子,娶个好媳妇,自己过日子,省得在家受气。”那时,我没有想到上大学,更没有想到来首都生活,做梦也没有想过从事外交工作。
图为贝宁总统克雷库接见中国文化代表团
我的继母一向还可以,不能对她有太多的苛求,说实话,她也真不容易。但有一点使我最难受,那就是:每当明明是我做错了事,她不说我,不骂我,而是恶狠狠地骂我的弟弟,打我的弟弟。我觉得:真比骂我、打我自己还难受。那时,我虽不懂多少大道理,可是自尊心极强。我想,要是我自己的妈妈就不会这样。我的两个姐姐也十分难过,常常三姊妹躲在一边偷偷地哭,怀念自己的妈妈。
我们家乡有一种说法:“宁死做官的爹,不能死要饭的娘。”这句话我的体会是极其深刻的,具体的,实际的。
如今,当我看到自己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都有自己的母亲,可以得到无限的母爱,可以依偎在母亲的怀里撒娇,我感慨万千,真是:“世上只有妈妈好。”我羡慕这些孩子即使做错了事,被自己的妈妈痛打一顿,那也是幸福的,心甘情愿的。
我曾经历过这么一回事:刚解放不久,我差不多十一、二岁。那时我在离家十多里路的团堡镇上白家寄读小学。每个星期六放学回家,第二天,即星期日的下午,背着苞谷面、毛毛菜、柴禾、油盐再返回去,平时上学自己做饭吃。
一次,我回家,正巧家里喊活路(集中找人帮忙突击干活),磨了一盆豆腐,于是我就拿了几块准备带去上学作菜,眼看我的伯娘(称后母)不高兴,便扔下豆腐就回镇上去了。那一个星期,我除了喝玉米糊糊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菜可吃。有时好心的白家人看我可怜,顺便给我点咸菜什么的就饭。
文隆胜在法国陪肖特夫妇出席中国文化周年
早熟的童年每个人的童年都应该是天真无瑕,活泼可爱,无拘无束的。
可我的童年却不是,首先我早早地就没了自己的母亲,我父亲又是一个十分严厉的人。我们家不仅大人有整天忙不完的活,就是孩子们一点也闲不着。所以,我一点儿大,就开始做事,放牛、捡柴、割牛草、打猪草、拾粪、编草鞋……我都干过。
有一回,我还很小,我们家在十多里外的安乐乡山上包了几棵松树,伐倒、锯断,劈成块块柴,准备干了后挑到街上去卖。我从山上往下运,一次虽只搬几块,也累得我够呛,腰酸腿疼了好几天。
我们农村别人家的孩子,可以捉迷藏、打陀螺、放风筝、掏鸟窝,而我呢?可怜哟,什么娱乐也没有。大约我十来岁时的一个春天,我也做了个竹架糊的纸风筝。鲢鱼随着微微的春风摇头摆尾越飞越高。
当我玩得正开心的时候,我放的牛下地里吃庄稼去了,又被父亲发现。我父亲顺手操起一根竹竿跑过来狠狠地打了我一顿,连竹竿也打裂成几块。从此,我再也不敢疏忽大意,不敢轻易地玩了。
我做事有时完不成任务,也会做假哄人。一天早晨我上山放牛割草,该到回家的时候了,草还没有割多少,回去怎么交代呢?我想出个办法:在背篓的缘边插上一排小树枝,把割的草全堆在上面并用葛藤围起来,显得满而高。这回总算过了关。据我记忆,在我所有干过的活中,最使我讨厌的是夜里磨苞谷和裹烟叶。
我们山里人,主食以苞谷和洋芋(土豆)为主。三天两头得磨苞谷面,而且常常是在晚上,那石磨又重又笨,一圈又一圈且磨不完,打盹还会磕在磨盘上。当然,做这种活,不是我一个人。有时跟我姐姐,有时跟我伯娘。即使只是做个帮手,比如,喂磨(往磨眼里添苞谷)也够我烦的了。因为太晚,时间太长,小孩子不是觉多嘛!
我们家乡的主要经济作物就是生产烟叶。现在主要是生产烤烟,那时候不是,是卖给别人直接卷起来抽的条条烟。烟叶割下之后,先用草绳串起来凉晒,等凉到一定的程度就要裹烟,就是把宽烟叶裹成条条形。这工序要反复多次,而且只有等到半夜下雾了,烟叶才能回潮,这时才能裹。你想想,一个小孩子,瞌睡又大,哪能熬到这么晚呢?
有一次,我大约才八、九岁,夜里勉强被我父亲唤去裹烟。烟一排排地凉在吊脚楼的彩楼上。我们家那个彩楼当时还没装栏杆,因怕雨水把木板淋湿,就用杉树皮临时覆盖着。裹着裹着,我一脚踩在衫树皮上,沙树皮一滑,哎呀!我差一点掉了下去。
不知怎的,可能是人的本能作用吧!我伸手抓住一根凉衣杆,这吓坏了父亲,他赶忙过来把我抱住,才没有掉下去。彩楼离地面差不多有六、七米,满地都是乱石头。那回要是掉下去,恐怕不是死,也得残。想起来都叫人后怕。左邻右舍都说我“命大”,说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文隆胜、霍敏芝在巴黎凯旋门留影
由私塾
到学校
我在贺家坪读了一些时候以后,记不得是什么原因,又转到沙地沟去继续上学。
沙地沟的学堂设在当地一家有名的大地主冉德卿的住宅里,私塾先生也姓冉。我每天背着木匣子书箱,书本、笔墨在里面来回晃荡、碰撞,我持一根防狗的紫竹棍,丁宁当啷,早去晚归。我手里提着一个小竹篓子,里头装着苞谷面面饭。中午在学堂附近农家借火热一热就吃。我们山里人,心眼儿特别好,他们不仅乐意接受,有的人家还主动给点菜。
我学习一直不错,先生挺喜欢我,同学关系也很好。我在那里一直读到年解放。
解放后私塾取消了,我不得不到更远的团堡中心小学去读书。在私塾只注重文学训练,不教数学知识,我转到团堡小学时,年已十一、二岁,因为算术基础差,只能从四年级读起。尽管如此,开始我的算术课仍比较吃力。不过,很快我就开了窍,不久,我不仅赶上了别人,而且同语文一样,成绩进入前三名。
头一年年终考试,我本应得 名,一名姓孙的同学学习也很好,他的父亲又是原来农村的一位私塾先生,颇有点名气和影响,就把他定为头一名。为这,我好久了心里还不服气。
多亏我知道努力用功,能吃苦耐劳,在学校里,什么洒水扫地,抹桌凳擦黑板,我总是事事在先。我的口才生来流利,学校举行演讲比赛,我居然得了第二名, 名是比我高一级的姓*的女同学。在老师们的眼光里,同学们的心目中,我颇有点威信,像个小大人,第二年大家一致推选我担任学生会主席。
这段时间我的生活仍旧很艰苦。由于路程实在远了点,不可能每天回家,两种寄读办法我都尝试过。
一种是住校。十多个人挤在一间阴暗潮湿的房间里,睡在上下两层的床板上。每个人交一定数量的苞谷、*豆、蔬菜和少许杂费,由同学们轮流磨成苞谷面和合渣,由一名校工帮忙蒸煮,供住校的学生吃。
合渣是当地普通老百姓常吃的一种菜,就是先将*豆用水泡胀,连豆子带水一块儿磨成浆,煮开,不过滤,再加一把青菜或葱及一些咸盐。有苞谷面蒸成的饭,有*豆合渣作菜,肚子饿了吃起来还是蛮香蛮香的。知足的乡亲们历来有这种说法:“事事都是假,面饭泡合渣”。
比住校更省一些的,那就是在镇上找一家熟人寄读,星期六回家背粮食背柴禾,平常自己做来吃。
总之,无论在家里也好,在学校也好,还是在人家寄读也好,我的生活都过得十分艰苦。那段时间里,除过年外,我们家平时大约个把月才能吃上一顿肉,人们习惯叫“打牙祭”。那时人们上街买肉,不像现在,见了肥的就摇头,一般都爱买肥的,吃起来过瘾、解馋。看来“挑肥拣瘦”的说法不合时代潮流了。
我星期天回到家,两个姐姐心疼我,偷偷地给我煮碗面条,再加两个荷包蛋。我狼吞虎咽送下肚里,不知有多好吃,这里包含着两个亲姐姐的多少情意啊!
一次火灾解放后我去团堡中心小学读书。
学校位于团堡镇街东头外,由两栋二层木结构楼房教室和中间一排教师办公楼连接成一个H型,办公楼底下是礼堂,后边有几间破旧的平房。房屋虽差,设备虽然简陋,可这是全区的文化中心和 学府,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可称着“殿堂了”。我在这里学习,寄宿在镇上白家。
白家以作小买卖为生,卖些烟酒、糖果、日用品。白家跟我家非亲,非故,但白家为人厚道,愿意为我学习提供方便。我从心里十分感激他们,虽说不给他们惹事,总还是给他们添了些麻烦。
一天,我们正在上课,忽然听见有人喊“失火了!失火了!”全校各班师生直往院里跑,一个个既惊又吓,乱成一团。有的试图冲出学校,回到家里看个究竟。不知是谁把校门的铁栅栏关上了,死死地把住,不许任何人出去。
学生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有的抓住栏杆直嚷:“天啦!我们家被烧了。我们家怎么样了?”熊熊的烈火直冲云霄,噼里啪啦,那一栋栋木头房子就像纸糊的一样,倾刻间烧个精光。
过了好几个小时,火慢慢熄灭了,能着的都烧了。这天放学特别晚,街上的孩子有的已无家可归,我寄宿的白家也在受灾之列,我仅有的一条被子和简单的用品亦化为灰烬。我无处可住,只得摸黑回家。
街上的房屋大部分都被烧了,一片惨景。失火的原因我一直不知道,也顾不得去打听。剩下的房屋是如何保住的,我倒听到过传闻。火起来了,越烧越猛,越烧越旺,有一家姓肖的两兄弟眼看全镇都有被火神吞食的可能,他俩爬上房,掀开瓦,用斧子砍断梁,然后下来,大家齐心协力把墙推倒,这样将正在着火的和还没有被着的之间形成一个隔离带,等火势到达时再无法蔓延下去,从而保护了一部分房屋和家庭幸免于难。
我后来长大了,回忆起关大门把栅栏的那位实属伟大,否则,一帮孩子冲到街上去,帮不了忙,光添乱不说,弄不好还有可能烧死砸伤几个。
团堡镇虽不算漂亮,但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有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石龙寺,有清朝道光年间建造的培风塔和清朝咸丰年间建造的宜影塔,都是研究巴文化和土家族民风民俗的好地方。
我多年一直思念着它,留念着它,年夏天途经此地,还专门去小学校看一看。如今,学校已面目全非,那两栋木质校舍尚存,但似乎变得更小更旧了,其余部分已全然变样。
老街仍在,旁边又建了一条新街,有国道通过,比过去显得繁华多了,甚至开始带有一点现代的气息了。不是吗?过去哪有钢筋水泥建造的房屋,哪里有汽车从这里经过呢?再过若干年,古老的团堡山镇一定会变得更美、更漂亮。
简讯定了:三节下周二开始
4天时间,3台晚会
晚会顺序
天19:30,英语戏剧专场
第二天19:30,高二年级晚会
第三天19:30,高一年级晚会
《三节视窗》记者团安排三节采访工作NEWS
﹀
﹀
﹀
记者团
推荐阅读:
今年三节有好“戏”看了
三节十宗最:恩高人玩嗨了(值得珍藏)
从饿饭到冲饭
文隆胜寄语青年“珍惜今天”
赞赏
人赞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