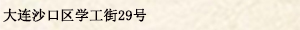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爱
韩综《无限挑战》里,我从一首节目嘉宾的原创rap里第一次听到尹东柱的名字,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说唱歌词里听到有关爱国的故事,抛开国家背景的因素,这种文化输出是可敬的,独立、自由、不拘泥于情爱男女的小事,反而用小众去融合小众,来创造一种全人类都能共情的人文价值。
前一段歌词“一颗星是回忆,一颗星是爱恋,一颗星是孤寂,一颗星是憧憬,一颗星是诗歌,一颗星是妈妈。”取自尹东柱《数星星的夜》里的原句,在诗里那一句是惆怅且含蓄的,糅合了对母亲的思念、对美好记忆的回想,对人生遭逢境遇的思考,然则又欲言又止,要知道那是在日本侵略亚洲的时候,所以所有的希冀与渴盼都只能轻轻被压抑着,化成后来诗文中的那句“在那掩埋我名字的山坡上,漫山遍野的青草,骄傲地生长”。
但歌词里,创作者却在后面填道:“不能愧对于我的名字,我的国家,今天也向前一步,使不被埋没在泥土。”我相信他是读懂了这首诗的人,从母亲落在故乡,从星星落在希望,从掩埋名字的山坡落在向前一步的祖国,他把诗人含蓄的盼头给写明白了,就像是将战争年代的厚厚阴霾渐渐拨开。
我想若要以诗或以歌共情,非得是热爱不可。
可我那时还不知道,写完这首诗的尹东柱在两年后,便因参与反日民族独立运动被捕入狱,再两年后,他死于牢中,年仅28岁。直到四十年前,尹东柱的弟弟才将他的遗稿在韩国发表,人们也才开始认识这位了不起的诗人。
热爱与追忆或许无法对抗残忍的现实,可对当初的尹东柱来说,他用“泥土掩埋了名字”,何尝不是已经打定主意,与那现实死磕到底。
在尹东柱的另一首作品《向阳坡》中,他在看着两个孩子在玩争地盘的游戏,便感到担忧,因为“担心原本就已虚有的和平,再次一朝破碎。”而更具讽刺意味的句子还在前面——“在谁是主人都不知道的土地上”。土地无法言语,但诗人仿佛听到远方呜咽的哭声,再联系那首《数星星的夜》,诗人正是用这样一遍又一遍呼唤所有人名字的“笨拙”方式,在默默对抗殖民体系下,大众对于身份认同和自我归属的矛盾化危机。
文明被逐步摧毁,文化被逐步侵蚀,也许下一代,再下一代,人们再也不记得他们曾经的名字,只以为脚下土地的主人便是他们的“主人”,但是历史可能会撒谎,可艺术不会,诗人有义务也有责任将这一切反映在笔下,因为我们笃定,总有一群人会立在那里,始终坚持。
小孩子无法理解大人们的悲哀,越清醒的人在此刻则愈加痛苦。好的诗人,绝对不会允许将一段不痛不痒的文字塞进人们的手里,爱国诗人更是如此。所以文人执笔就要像将军拿起刀枪,非得战胜些什么才能停止,他们深知想要掌握“文字”这门武器的力量,那必定需要对世界抱有敬畏与责任。
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
当我看到这本尹东柱诗集的名字《痛哭如歌咏》,脑海中立即浮现的便是这句清代前人说写的话。为什么而感到痛哭呢?生于吉林省一个普通教师家庭的尹东柱,求学阶段先后辗转中韩日三国,所以于他本人而言,所说的反战不仅仅是抗日战争,而是针对所有的极端主义的侵略,年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年日本占领东三省,可以说在尹东柱短短28年的人生旅程中,眼前所见皆是侵略与殖民。
这样的环境,对于一个时刻提醒“我的名字”的诗人是无法忍受的,他在那些注定无法见诸报端的诗里痛哭又不放弃寻找希望:
《十字架》里,他写下“垂下头颅,让鲜血像绽放的花朵一样。”,即使那十字架在高悬的塔顶,也想学着耶稣那样,可以用一死来换取新生;《八福》里,他一遍遍重复着“哀恸的人是有福的”,自我麻醉吗?并不是,这是警惕和鼓励,是相信未来还有美好可期的坚持,所以“我们将永远哀恸”;《闭着眼睛走吧》里,他告诫着人们“天已经黑了,索性闭着眼睛往前走吧”,用黑暗中的双脚丈量出一段新路,“将拥有的种子,一边播撒一边行走”。
燃起希望,又被现实打败,痛哭,又重新找回希望。陷入如此循环中的人们,有的消失在漠然与迷茫,有的沉沦在阴霾与海洋,有的人,则如尹东柱一般,勇敢地活下去,为了和平奔波至死。因为如他本人所写的那样“我活着,只是为了寻找丢失的所有。”
如果用一首诗来概括尹东柱的一生,非他本人所写的那首《序诗》不可:
直到死亡那一刻让我仰望天空心中没有丝毫愧疚树叶上轻轻拂过的风也使我心痛我是要以赞美星星的心去爱正在死去的一切去走指定给我的道路今夜,风依然掠过星星
在诗人看来,死亡的一刻并不是时间的终止,他的反省自悟、他的问心无愧、他的负重前行,都会在死亡时给予时代一个答案,让冰冷的现实在温柔炽热的心中安全着陆,让未来终将吹来的风将此时的星星点亮。
在诗人的眼中,星辰、天空和晚风,是最常见的意象,在它们的反面通常立着的是黑夜,这种呈共生又对立的关系,代表的正是尹东柱本身内心的复杂世界,既夹杂着对未知的不确定与孤独感,对多舛、艰难命运的反抗精神,也包含着他最单纯也最直接的期待。也许黑夜浓稠地无法化开,可风会从天空吹来,星星无法被阴霾抹去,但我们只要耐心的等待,总有光会照进来。
每个时代都需要这样的人出现,可同时代的大多数又无法理解这种情怀,只把它看作鲁莽和执拗。诗人理解这些不解,也从不在意外人的眼光,只做自己的坚守。正如他在致敬俄国著名文学家屠格涅夫时所写的那首诗,他看见衣衫褴褛的穷苦少年,内心恻隐,却只看见:
第一个少年只是回头用充血的眼睛瞥了我一眼第二个少年也只是这样。第三个少年也只是这样。然后好像是在说这些事情与你何干……山岭上什么人都没有,只有越来越深的黄昏汹涌而来。
黄昏之后,倘若人们都将苦难当成了习惯,那么黑暗必将到来。
在屠格涅夫的短篇《白菜汤》里,一个农家的寡妇死掉了她的独子,地主夫人在下葬时前去探问,看见寡妇在家中,从锅底舀起白菜汤来,一勺一勺地吞下。夫人想起自己女儿死去的那段日子,自己无法享受任何生活的乐趣,所以她无比吃惊这位母亲在此刻为何还有这样的胃口,寡妇流着眼泪继续吞咽的食物,说道“我的日子也完了,我活活地被人把心挖了去。然而汤是不该糟蹋的,里面放有盐呢。”
夫人无法理解是什么,只是耸了耸肩,就走开了,在她看来,盐只是不值钱的东西,站在不同阶层的人,望向对方,只能看见自己内心的情绪,却永远无法解读对方的选择。
那有什么要紧的,那只是盐啊?
那有什么要紧的,那只是个名字啊?
那有什么要紧的,那只是苦一点啊?
那有什么要紧的,那只是一片黑暗啊?
没有什么值得悲哀,或许在尹东柱看来,才是时代最大的悲哀。所以总有人得去在意这些故事的,在咀嚼小小的悲欢中,看到更大的世界。正是这种超脱了大时代背景下个体的情怀,才让尹东柱最终成为中朝共同认定的爱国诗人,他的遗骸最终被父亲接回埋在了日思夜想的故乡的土地上,他的名字也最终被许多人提起并记得,他所期待的,那个更好一点的未来,已经实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