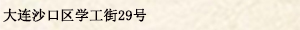原创专栏你怀里抱着你傲骄的狗,我就想
大人们养鸡,目的总是恶*,先吃其蛋,再食其肉。
虽然嘴馋的我们也是蛋肉皆好,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付出赤裸裸的真心。
只是童心稚嫩,也就是那么几年的功夫,渐渐看惯了聚散来回,也就习惯了对万物的索取,渐至麻木。
或许是忘记了,这世上的每一份相遇,都是亲密的缘定。
01、我家战斗鸡
从开始有了记忆起直到十八岁,我都是生活在工厂家属院里的孩子。
从化工厂到毛纺厂,从妈妈的厂搬到爸爸的厂。机器的轰鸣声听惯了像歌,常来常往的面孔没有不熟悉的。
那个时候,我们的名字从不叫某某,而是某某家的丫头/儿娃子。
我关于养鸡这件事的人生初体验,其实是带着恐怖色彩的。
从我四岁记事起,是住在化工厂家属院的一处小院落里的,我妈是子弟学校的老师,我爸是远在城市另一头儿的农机厂的工程师。
我爸比嗜工作如性命,一年里感觉有一半多的时间都在加班出差。于是,我家养了一只大公鸡,看门……
鸡生如人生,最终能成为什么样的狠角色,都与自己的努力进化分不开。
最早之前,我家院子西头靠墙的鸡圈里,是有着公公母母几只鸡的。
后来随着成长,渐次成年的鸡们就各自显露了不同的个性。
除了这只彪悍张狂目中无人的货外,还有温文尔雅的公子,打起鸣来都像吟诗;有寡言恬淡的小姐,吃起食来不争不抢端着身份;还有那小丑一样两面钻营的,这边被叨烂了鸡冠灰溜溜地缩回凡间,疤还没结利索呢就又前去献殷谄媚。
可以料想,一只鸡中霸王的崛起,势必是建立在周围角色惨遭荼*的背景下的。那圈里时常是鸡血四溅鸡毛飞。
它让同类不聊生,它狂妄残暴,但它却又深谙生存之道,不但忠于主人(至少是我爸妈),提防外人,打鸣还格外响亮。
那中气十足的嗓音、彪悍的体格,昂头挺胸的姿态,至今想来,实乃公鸡中的忠犬战斗机二合一。
身为一只鸡,它的内心却澎湃着一条看门狗的高尚情怀。
我家院子北面是一间客厅套着一间大卧房。起初,为了把战斗鸡和其他凡俗的可怜鸡隔离开来,我爸用了一根两米见长的绳子,把它拴在了墙角。这两米的活动范围,既可以让他看护家院,又能约束住它的冲动。一旦得到了这两米的自由,它更是把自己当狗一样的来劲了,但凡院子里进了人,必要勃然大怒,咕咕咕咕的尖利啸叫,一边叫还一边扑腾着往来人的身上飞。
如果不是被绳子掣住腿脚,他只身斗个壮汉三五回合也是不分胜负的。
那气势,真真已然盖过了隔壁家的大黑狗。直到大人出来,一声斥责,他才悻悻地收了翅膀,嘀嘀咕咕不情愿地退了下去。
那个时候,我的姐姐并没有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而我的弟弟还忙着扒在铁栏杆床上糊各色地图,因此在战斗鸡眼里,除了我的父母,就数我跟他脸熟了。
可是,势利眼如它,竟然不买我的帐!
我家邻居有个白胖小子,大约和我是同一年的。我俩常常一起玩耍,不是去他家,就是在我家。
每每进他家门时,他家的大黑狗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叫也不叫,顶多抬头白我一眼。
可他但凡一进我家门,那嗜血大公鸡总是恨不能扑上前去,在他白白嫩嫩的脸蛋上撮上两口。它简直是人家的童年噩梦!
所以,每每来找我玩,他都不敢贸然进门,而是在门口大喊我的名字,直等到我拎个扫帚疙瘩出门,恐吓那鸡一番,再将他迎了进来。
每每我狐假笤帚威,那鸡都是一脸不屑愤愤然,果然有一回,就瞅准了我回身进房门的功夫,出其不意地作势一扑,挣断了绳子,追上来对着我屁股就是一口……
让你逞能!让你逞能!
我嚎啕大哭,它挨了一顿胖揍。从那以后,它还是回到了它的圈。
什么年代都不少坏人,虽然我家靠院外的窗户都开得老高,可还是屡屡有几次,发现了踩着砖头偷窥的男人身影。而我家这只悍名远播的暴戾公鸡名声在外,竟无形中在事实上和心理上成为了我们的双重保护伞。
基于这个缘故,后来,看不下去每天上演的鸡圈血案,我父母选择连下蛋的鸡都宰了放它们解脱,但还是独独留下了始作俑者的它做光棍状活了很久。
这只孤独的公鸡在鸡圈里常常莫名生气,气到不行,把冠子套进网兜状的围栏里又大力挣脱,它的蛮力实在太大,屡屡撕裂了鸡冠,那圈里依旧见血,只是换成了它自己的血。
它是什么时候才解脱的,我已然忘记了。02、短命小萌货
等我六岁半之后,我爸他们的农机厂居然改头换面成为了一座毛纺厂,我家也在家属区分得了一块宅地,盖起了一座院落。我们搬家了,我也转学到了就近的市属小学。
而此时我们之前居住的化工厂已走到了破产边缘,在我转学之后的第二年,工厂子校解散,我妈的工作也调动到了我的新学校。
在新家的入门靠墙处,我爸带人挖了一口菜窖,挖完后又觉得不甚结实,没敢启用,那阴冷的地窖很快便成为了昆虫大百科基地,屎壳郎潮虫蝎子蜈蚣出没,连我爸自己都觉得瘆的慌。只得严严密密地封闭了出口弃用。
在那口菜窖上面,有一座铁笼子鸡圈。大部分的时光,那里是空着的,或者是我渐大,不再为这些事情倾注太多感情故而遗忘了。
倒是剁鸡食的记忆,还是清晰。
院子里墙边上有一把生锈的菜刀和一块旧案板,我妈买菜回来,经常给鸡们带一把小白菜,我拿两块砖头,把案板垫起,剁去了菜根须,把一棵棵的菜码得整整齐齐,细细切成小节,再混乱剁碎,刨进食盆,拌了各种谷物磨碎混杂的鸡饲料,一股子腥味,塞进笼里,鸡们就咕咕咕咕地炸锅了。
这般伺候过的,都是大人们的鸡,不是我的。
我曾经缠着我妈给我买过五只小鸡,用盒子养的那种乳*小萌货。不知是抚弄太多,还是命运本多舛,它们竟一只也未能活到成年下蛋挨宰。
那个时候,房里院里进进出出,没带钥匙门被风带起锁住的事情是常有的。
一天中午,天儿起了风,我一个人在家,惦记着我的小鸡崽就往外跑,刚出到院子,房门砰地一声被风刮上了。进也进不去,穿的又单薄。我只好把我的小鸡崽们连盒子端到厨房门边,躬着身子护住它们。
风越来越大,很快土裹着雨滴子砸了下来,小鸡崽们叽叽乱叫,我一时情急,便一只只捉起它们,塞进了我的校服里。
那个雨天,有一只小鸡崽就那样在校服里一路爬上了我的肩膀,安安静静地卧在我的肩头上,我一手轻抚着它,微微地偏过头,让我的齐耳短发垂下来,做它的屏障。
没过几天,它们陆续都死了。我没有淋感冒,可是我很伤心。
03、一册鸡毛本
我姐从小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她从小就一身文艺细菌泛滥,提起笔来能画出连环画,一张口就是一段传奇小说。加上一头卷毛大眼睛白皮肤高鼻梁子,那模样就像画张里跳下来的洋娃娃。我简直把她崇拜地跟头绊子的。
我姐小时候有一个笔记本,一直到她上初中还珍藏着,那里面每一页都粘着一根鸡毛,鸡毛旁边依次写着各位毛主的姓名、颜色、特征、生卒年岁,尤其是还附有一段小学生体的描述。
那个时候,流行贴画抄歌词本,她对她的鸡毛本比歌词本看重多了,一直到歌词本散了页,鸡毛本还是整整齐齐的。
有一年到了宰杀季,我爷爷居然决定一举宰杀两只鸡。我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坚决抗争,全家人轮流上阵劝说。她的鸡也感觉到了厄运将至,瑟缩成一团窝在她的脚边。
我内心里一边与馋虫恶斗,一边安慰我姐,旗帜鲜明地指责大人们心太狠。
后来两只鸡都被宰了,我姐躲在后院儿里大哭,一直哭到鸡肉都快做熟了眼泪还是不断线。
渐渐的,那香味阴险恶*地弥漫过来,我内心挣扎了很久,还是举起了白旗,我摇着她的胳膊劝说,“姐,都已经熟了,我们还是去吃一点吧……”
她用她那泪汪汪的大眼睛瞪着我说——“滚!”
我卑鄙地记得,那天的大盘炒鸡很好吃。
如果那两只鸡都是我养大的,我应该不会做叛徒吧……
PS:
大盘鸡是新疆名菜,据说最早出现在沙湾县。主要用料有鸡块土豆红辣皮子青椒块,皮带面是一定要有的,后来出现了各色改良版,有的在浓厚的汤汁里铺上了馕饼子切成的块儿,有的取酸菜之爽口提升味觉层次……我个人对香菇宽粉改良版颇为钟爱。
对于大盘鸡的创始人,目前还没有官方定论,但根据《大盘鸡正传》一书的作者、沙湾县*法委副书记方如果的调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沙湾县李士林开的饭馆里,他推出的一道“大盘辣子炒鸡”,正是后来的大盘鸡。
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那一天,我姐养大的那两只亲爱的老母鸡,被开膛破肚烫皮拔毛之后,我厨艺高超的奶奶现场就炒了两大盘,红辣皮子青椒鸡肉块,没有土豆皮带面,那味道,啧啧,却也是一绝。
本文作者:北飞烟子
如需转载,请联系小编。
北京治疗白癜风哪里医院最专业北京治疗白癜风哪家医院比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