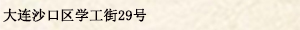开水白菜的关键,其实是ldquo开水
生于年的郭薰先女士,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年临近新年,她们家里请了一名打扫卫生的“临时工”。因为是新来的,对大家族里的情况自然不了解。她打扫完一圈路过厨房门口,发现两个木桶,里面装满了热气腾腾的开水,心想:干完活洗个热水澡正好。于是就拎着水桶到了院子另一边的淋浴房……过了一会儿大厨出来了,四下一看、暴跳如雷:我的汤呢?
我问郭女士:后来呢?她说:后来我就不知道了!作为民国时期四川荣昌县望族家庭的幺小姐,在未出嫁之前是不能进厨房的。姑嫂们闲聊,这个故事才传到了她的耳朵里。不过,我丝毫不怀疑故事的真实性,因为高级川菜的“清汤”,没有一丝杂质、装在木桶里,看起来就是开水无疑。
虽然酷似开水,制法却大有讲究:用老母鸡、鸭子、猪排骨、火腿蹄子等洗净放入锅里,加水、姜、葱、绍酒,烧开以后撇去浮沫,转小火慢熬。厨师有云:无鸡汤不鲜,无鸭汤不香,无骨汤不浓。味道的交融本身已经非常鲜美,但这只是开始。
约两三个小时后,捞出汤里的食材。把瘦猪肉茸(红茸子)放进盆里,加冷水稀释成浆,专业术语叫“解茸子”,然后将肉浆倒入热汤锅里,等待片刻,伴随浮起的血沫、转粉的肉茸,汤也从灰白色变得越来越澄澈。然后再用鸡脯肉茸(白茸子)水浆重复一两次同样的过程,由此得到清亮透明的“特级清汤”。
高汤之所以浑浊,是因为含有不溶于水的颗粒物(如油脂、 、其它蛋白质等)。“清汤”过程中,肉茸相当于凝絮剂,本身含有蛋白质,是疏松多孔的结构。蛋白质进入水里会电离,产生正电子或负电子,把颗粒物吸到疏松多孔的结构里,使之集中并悬浮。提前“解茸子”的目的是使肉茸均匀、快速地散到汤里,增大接触面积,提高吸附性。
开水白菜
喻家厨房,Chino摄影开水白菜是川菜里的一道名菜,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在川菜中 筵席上才可能吃到的。从我的描写里不难发现,费神费时的,是清汤,所以这道菜的重点, 不是白菜——白菜做成花儿,不也还是白菜吗?同样的道理适用于肝膏汤、鸡豆花、竹荪鸽蛋等“清汤+X”的菜品。最初我也不懂,所以斤斤计较鸡豆花的软嫩,*佑仁先生跟我说,吃鸡豆花其实是吃汤,我体会也不深刻。直到在一家餐厅吃到了泛酸的清汤——整道菜都被毁了。俗话说“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没想到反过来同样成立:一锅坏了的汤,里面放山珍海味也不会好吃的。
清汤为什么会变酸呢?因为放久了——汤里始终有水溶性蛋白质等,微生物在里面代谢,产生诸如柠檬酸、 、 等有机酸。隔夜的清汤虽然没有*,估计也没人爱喝了。厨师做清汤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像我上文所述,一次清好一大桶,这通常是五星级酒店等用汤量大的厨房的操作;还有一种是把扫汤用过的猪肉茸子压成饼、和鸡鸭一直小火放在锅里慢慢“吊”,要用的时候,单独舀到一个小锅里,再用白茸子清汤。后一种做法是过去川菜馆常用的,因为喝得起清汤的顾客不多,索性用多少“清”多少。
物资匮乏的年代,吊完汤以后,炖软的食材还要再利用:鸭子用来做蛋酥鸭子,棒骨上的肉也要剔下来……说起来算是“废物利用”,不过先别替食客生气,因为类似的利用非常巧妙:据王开发先生讲,吊高汤以后的棒骨上还有不少剔骨肉,先是作为厨师的伙食,天天吃也吃腻了,曾国华先生和张松云先生一商量,想出来一个做法,把软烂的肉剔下来,加几片玉兰片,剁几刀,加入全蛋、盐、姜米、豌豆粉、花椒粉等搓成肉丸子,然后按压成饼状,放入油锅里炸酥。 像切炸猪排一样切成长条,镶一些生菜,作为筵席上的“形菜”上桌。在上世纪80年代的荣乐园,这道“香酥肉”颇受顾客欢迎,外酥内嫩,咬开里面有肉有筋,不少客人还专门点这道菜!
大刀金丝面
玉芝兰,敏敏摄影据说“开水”的做法是借鉴自淮扬菜,我没有仔细对比过。
法餐里的“清汤”(Consommé)是在肉汤里加入肉糜、蔬菜、蛋清组成的混合物(Raft), 同样是打捞浮在表面的物质,也同样需要全程小火。
长发街的“玉芝兰”是成都少见的私房菜馆,主厨兰桂均先生以一己之力经营着小而美的餐厅,烹调的菜品里既有传统川菜的影子,也融入了粤菜、日料的技法。其中有一道“坐杠大刀金丝面”是以高级清汤配以类似广式竹升面的金丝面,形味俱美。可惜的是,不少美食作者都把重点放在了“面”,大幅描写面皮“薄得透字,大刀切得细如发丝”, 的部分却仅以“清汤”二字一笔带过,我以为这是“买椟还珠”,没搞清重点。
不过,追求形式复杂、讲究表面光鲜,而忽略实质的情况,在当下中国社会,还真是不少见啊!
文:尔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作者,以示尊重。
惟味与色无可争
我是尔雅
| |